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逐渐从国家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模式,转变为市场独大的“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高房价社会的产生正是市场力量全面渗透社会的产物,民众和国家经济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生活成本、经济成本,乃至社会成本。更为严重的是,房地产投机使得少数富裕阶层垄断大部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加深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为此,韩国知识分子在近几年掀起了反思房地产的热潮,认为房地产是综合诊断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内视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批评家孙洛龟所著的《房地产阶级社会》,他首次提出了“房地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并积极探索治理良策,引起了学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
一、理论贡献及房地产阶层定型化社会孙洛龟在《房地产阶级社会》一书中十分敏锐地从韩国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房地产话题入手,梳理了二战后韩国房地产投机的发展史,并运用大量国家与民间机构的统计数据,科学证明了房地产行业的异化发展对于产业结构转型、阶层固化、贫困问题、教育资源分配、生活质量和医疗健康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该书首次提出了“房地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房地产转向,对于依靠房地产行业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理论和反思的意义非常重要。概言之,该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
(一) 关于土地的“本体论”反思房地产行业是将土地和建筑物赋予商品属性,作为经营对象,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房屋的转让、出租、抵押等经济过程中赚取商业利益。该行业是民族国家追求现代性的产物,其本质在于人们的“土地观念”发生本体论意义上的改变。(1)土地的主体性。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土地不再被视为与人类同等重要的自然主体,而是赚取利润和满足私欲的客体化手段。土地空间环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分割和破坏,颠覆了土地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此,孙洛龟认为彻底解决房地产社会问题的前提在于重新审视土地对于人类生存的本体论意义,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土地犹如母亲一样,孕育世界万物。这是自古以来处于人们世界观核心位置的自然观和土地观……我们还需要重新回到‘在天地之间修房居住’的朴素的常识自然观”(孙洛龟,2012:228, 234)。这类土地观念富有浓郁的东方式哲学色彩,强调“天地人三才”的和谐统一,也是反思东亚国家房地产发展的根本性思维框架。(2)土地的社会性。土地以及建之于上的住房在强调“家文化”的东亚社会中更具有安定性、乡土性和社会性等特殊意涵。对于人们来说,土地和住房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而且是人的延伸和家庭的载体。有了自己的土地或房子,才有家的感觉。因此,包括土地和住房在内的房地产财产在东亚社会里具有安身立命的本质意义,人们只有努力拥有房屋的所有权,最终才获得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因此,在孙洛龟提出的“房地产阶级社会”里,房地产资源被少数利益集团垄断,土地的社会性难以正常发挥,导致大部分年轻人推迟成立家庭的计划,由于高房价高租金,租房家庭过着频繁搬迁的生活,土地所内含的安定性也被彻底破坏。(3)土地的公共性。“房地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在本质上强调重新寻回土地的公共性,即房地产资源的分配应重视公共利益并彰显公正性。孙洛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的“私有财产第一性”原则不适用于房地产。因为土地不是一般商品,不能完全被市场性所掩盖,其本质是公共财产,应发挥国家力量保障土地的公共性以及大众拥有住房的公共权利。
(二) 阶级分析的房地产转向该书中的“房地产阶级”是在英国“住房阶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韩国高房价社会问题综合而成的理论概念。“住房阶级”理论的代表为雷克斯和默尔(Rexand and Moore)以及桑德斯(Peter Saunders)。1967年, 雷克斯和默尔在合著的《种族、社区和冲突》中首次提出了“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1984年, 桑德斯又从“住房所有权”和“消费社会”视角拓展了住房阶级的理论内涵。该理论总体上继承了传统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冲突论理论风格。但从阶级划分标准上看,该理论是传统阶级理论在后期资本主义的拓展,即马克思论述的阶级结构是由前期生产型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作为划分标准。但后期资本主义已进入消费社会,阶级的划分标准也应从生产性资源转变成消费性资源,特别是决定人们生活质量的住房资源便成为重塑阶级身份的关键因素。住房阶级理论的提出与英国新自由主义式社会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大力推行“国家退场、市场扩张”的各类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减少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鼓励人们自主买房,使房地产资源成为主导国家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因此催生了不同于生产性阶级的住房消费性阶级,而当今的韩国社会也有类似的转型背景。因此,孙洛龟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房地产阶级”秉承了“住房阶级”的理论优势,同时也弥补了后者的不足之处。
一方面,两者的相同点表现在:(1)在前提假设上,两者都认为剥削的本质已不再是资本家在生产领域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一个群体由于住房资源导致的生活机会的不对称生产,或一个群体依据住房资源的大小排斥另一个群体(Saunders, 1984:220)。“住房”代替“职业”成为划分阶级的关键因素。(2)研究的社会类型都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消费社会。新自由主义的前提是倡导无制度束缚的个体自主选择性,只有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才能促使商品和资本的快速流通和循环。尤其是作为“集体消费品”的住房,在日益缺乏国家制度保障的新自由主义社会里,已成为导致社会分化的决定性因素。(3)在研究切入点上,孙洛龟与桑德斯都从“住房的所有权”入手分析社会不平等,强调获得住房所有权的屋主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权力,反之则会在社会各方面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房地产阶级”理论也对西方的住房阶级理论进行了扩展。(1)房地产的整体性。一般而言,房地产资源同时包括地产、房产和楼产。孙洛龟因此采用了“房地产”这一内涵大于“住房”的概念作为阶级划分标准,以一种更为整体的视野来审视地产、房产和楼产等房地产资源对于阶级分化的推动作用。(2)房地产阶级的网络性。与西方“住房阶级”强调与“国家”或“市场”等单一因素的因果关系不同,“房地产阶级”的表述更强调东亚国家的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甚至是媒体权力与知识权力阶层之间,都易在房地产的发展过程中结成特有的利益投机网络,通过“共谋”的方式垄断房地产资源。孙洛龟形象地称之为“房地产投机的食物链”。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这个食物链上的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构成了六大房地产阶级。第一阶级为1户多套房群体,其内部又分为两种:一是处于食物链上层的建设业财阀、房地产官阀、政客、保守舆论媒体和学者,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房地产投机联盟(又被称为“房地产五敌”,即民众在房地产方面的五大敌人),二是包括社会名人和职业投机商在内的一般性房地产富人;第二阶级是1户1套房群体;第三阶级是虽然有自己的住房,但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过着租房生活的群体;第四阶级是能支付5 000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27万元)租房保证金租房居住的群体;第五阶级为支付5 000万韩元以下租房保证金租房居住的群体;第六阶级是处于最底层的无房者,包括租住在木板房、塑料棚屋和地下室等临时场所的极贫群体(孙洛龟,2012:44-45)。房地产投机食物链的社会资本依次递减,无房者成为完全被排斥于社会网络之外的最底层阶级。(3)房地产阶级与“土建国家”。产生房地产食物链生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建国家”的发展模式。“土建国家”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和韩国的一些政客利用行政资源,不断规划兴建道路、机场、房地产开发等大型公共土木工程,并且多为重复建设,其目的是赋予大型企业财阀的开发特权,从中赢得财阀的政治资金支持。因此,此概念成为学界对“土木工程型经济高速增长”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概念工具。“土建国家”模式的严重后果在于滋生官商腐败、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地域社会基础和文化、追求形式的结果主义、庞大的土建行业阻碍产业结构改革等(
孙洛龟划分“房地产阶级”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调“房地产资源”逐渐取代“职业”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而且还强调房地产投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房地产的影响像病毒一样,蔓延到生活方式、消费模式、教育资源分配和医疗健康资源分配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一旦在“房地产资源”上处于弱势,就会在社会的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最终走向恶性循环的贫困之路。因此,作者将这种一切由房地产资源决定的社会称为“房地产阶级社会”,其实质是一种阶层固化的定型化社会。1孙立平(2008:121)曾提出“精英联盟”、“寡头政治”、“赢者通吃”是社会结构定型化风险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结盟关系是定型社会的基本力量,但他并未明确指出何为定型社会的基本载体。孙洛龟结合韩国的高房价社会现实回答了这一问题,他鲜明地指出“房地产”是定型化社会的基本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房地产犹如一面内视镜,研究者借此可以洞察精英组成联盟垄断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韩国房地产行业逐渐形成了由政治精英和市场精英(尤其是房地产建设行业)通过“政经联合”、“政官(国有企业)联合”、“官(国有企业)经(土建公司)联合”等三种机制,再加上维护房地产合理性的学界和舆论界,形成一个“土建国家复合体”(
该书的前五章用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审视韩国房地产投机给全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语言犀利,批判深刻。但作者的目的并非仅在于表达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正如希望之光仍然普照大地一样,作者在第六章积极探寻治理良策。这些对策并非泛泛而谈流于形式,作者曾作为韩国国会议员辅佐官参与监督政府政策,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房地产对策。
总体而言,孙洛龟的房地产治理对策具有很强烈的“国家回归”取向,这与韩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国家缺失”危机密切相关。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从以前“国家主导式”的快速现代化模式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前者强调政府把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作为合法性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动员在调控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规划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后者则强调“国家权力和责任无限缩小”的另一种发展极端,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规制作用,减少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道德责任。尤其是作为集体消费品的房地产,其自身具有的以公共利益和公正性为标志的公共性,已逐渐被国家退场、市场扩张的模式消解。其中形成的利益集团极大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公共利益,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因此,作者主张国家应推行综合性政策,积极打击房地产投机势力,保护房地产弱势群体权益,彰显一种构建公共性的“国家回归”倾向。
具体而言,孙洛龟的房地产对策与其划分的六大房地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强调国家应针对每一阶级的特点,量身订制符合不同阶级利益的房地产政策,突出国家回归的层次性和针对性。例如,有房阶级并非铁板一块,拥有1户多套房的第一阶级是国家发挥力量限制和瓦解的对象,政策取向应是对现住房以外的以投机为目的的住宅实行宅基地2国有化,提高购置税和租金税收的比例,加强房地产投机收入的二次分配。第二阶级是1户1房群体,刚性需求较大,是房地产投机潜在的受害者。住房政策应重视和保护这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加强对其房屋维修翻新上的支援。第三阶级是过着有房但因经济原因不得不租房生活的“双重生活”群体,他们也经历房租上涨的痛苦,因此也是住房政策的主要保护对象,让其重新搬回自己的产权房。此外,无房阶级中也存在特点不一的各类群体。第四阶级是有能力支付5 000万韩元租房保证金的群体,如果房价稳定的话,他们有买房的潜力,因而强烈反对房地产投机行为和高房价。国家应消除房价泡沫,提供廉租房,给予居住补助金。第五阶级是典型的租房群体,完全没有能力买房。国家的关注点应放在消除其租房压力上,保护租客的合法权益。如保障租客10年内对租房合同提出修改和更新的权利,将月租金上涨率控制在10%以内,设立国家机构性质的“房租担保中心”,敦促银行提前放款快速解决房租合同到期时的房租保证金返还问题,以消除租房者得不到房东返还的房租保证金而搬不了家的压力。第六阶级为居住极贫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房地产投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该阶层的生活应全由国家保障,全面发挥国家公共性的作用。具体政策为改变“驱逐式”的城市开发政策,将保障人权提到首位,推动各类住房福利政策,特别是保障儿童、残疾人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第一要务是将其搬离地下室或棚屋等未达标住房,安置到政府修建的公共廉租房,加大房租贷款的力度和规模。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民间组织和当地居民的自我管理以及对市场的监督作用。总之,孙洛龟的政策建议是反思市场独大、国家退场的社会发展模式的产物,特别是对关乎全体民生的房地产问题,更是呼唤一种以民为本,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平衡发展的房地产政策,其本身具有的公共性、针对性和层次性等属性对中国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住房政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对中国的有益启示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众所周知,1998年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一词也成为中国老百姓最为关注的热门词汇。若从“房地产”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的变迁可视为从“单位中国”转变为“房地产中国”。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直接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的居住模式,即从“单位房居住”转变为“商品房居住”。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居住观念、交往模式、生活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也随即改变,并日益成为影响老百姓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近几年房价持续走高也产生了不良的社会现象,即日益突出的“富人穷人分开居住”的“居住分异”现象。社会分化逐渐表现为以居住形式体现出的“高档社区”和“弱势群体聚居区”(又称为“低保户聚居区”)。正如孙立平(2008)所强调的那样,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开始形成,居住的有形边界随即会引发生活方式和文化资本的无形边界,成为阶层结构再生产的重要机制。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亦可见到韩国房地产阶级社会的端倪。韩国作为一个曾遭受侵略、二战后由国家动员全社会资源走上赶超式现代化的东亚样本,其社会变迁逻辑和社会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因此,国内学者在选择欧美和日本作为中国转型社会的反思之镜时,不妨也可聚焦于韩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上,多一个参照框架,或许有益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与规划。《房地产阶级社会》一书在中国的出版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将会引发我们对于房地产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深刻反思。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该书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两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第一,该书的理论启示在于深入挖掘房地产的社会意义,拓展社会不平等研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发挥“居住社会学”的想象力,深化社会不平等研究。传统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主要关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涉及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变量与阶层分化和阶层流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随着城市化和房地产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居住问题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中介变量。诚如塞勒尼(2010:80)所强调的:“住房状况是关于流动性的一个中介变量。作为中介变量,住房条件跟比例失衡的人口生态分布相联系的话,它的效果可以在一开始就很明显。当糟糕的住房在空间上集中并形成贫民窟的时候,住房状况就变成了一种限制因素”。特别是在政治资本和市场资本相互交织和共生的东欧转型社会中,“居住”被视为社会分层重要的中介因素,“住房政治”也成为政治权力分配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国也与之类似。为此,边燕杰(2005)将居住分层和不平等问题视为检验市场转型理论争议的重要研究视角。他借助住房的产权、面积、质量等指标所体现的社会分化性,统计分析出管理精英的住房优势大于专业精英和非精英,从而验证了市场转型论只强调单一市场发展逻辑的局限性,强调中国转型的延续性和复杂性,即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遵循的是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并行的权力维续逻辑。此外,国内学者也日益关注居住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分化效应。如刘祖云和毛小平(2012)认为,中国城市住房分层结构是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李强(2009)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因住房的所有权、价格、地理位置、级差地租、社区环境和社区文化特征等居住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商品房户、回迁房户、单位房改房户、简易楼住户、廉租房户和传统私房户等六个住房地位群体,这些群体最终会拉开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所有这些关于居住分化的社会学研究无疑成为我们可以继承的“居住不平等研究传统”,扩展了传统社会分层的研究界限,将“居住”视为与收入、教育和声望等传统分层标准起到同等作用的重要因素,成为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特性和转型逻辑的重要视角。然而,此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诸如韩国房地产阶级社会研究关于土地观念的反思、阶层定型化社会、房地产发展背后的国家公共性回归等问题的分析所体现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有待深入发掘居住与收入、权力、声望等传统分层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居住作为中间变量发生分化作用的机制。
为此,研究者有必要将“居住分层”研究扩展到“居住社会学”的学科高度,从更为整体的视野考察居住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居住社会学”也称“住宅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国家创立发展以来,一直强调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多单元和多侧面的综合研究方法,即研究者从居住与社会形态相互影响、居住与社会多种因素、居住与社会关系、居住与社会发展、居住与社会制度、居住与社会问题、居住与社会物质载体、居住与社会居住行为,以及社会心理、居住与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住宅与社会对外开放等角度,研究居住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孙金楼,1987)。早在20世纪80年代,孙金楼(1983, 1987, 1990)和张仙桥等(1995)就强调在改革开放后房地产行业发展背景下进行居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积极撰文介绍居住社会学的内容,涉及居住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住宅建设预测、住宅社会消费、住宅政策的公平公正等方面,并以著书、成立各类住宅研究协会等形式积极推进中国居住社会学的发展。然而,正如张仙桥一开始就将居住社会学定位于“边缘科学”一样,该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式微,与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等学科相比,其理论话语地位仍处于边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高房价社会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寻回居住社会学的传统,发挥该学科的综合性优势,加强研究传统阶层分析中的重要因素,如宏观层面的国家与市场、中观层面的群体与组织、微观层面的职业与教育等因素与居住分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言,从内容上,研究者应综合分析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模式、政治权力分配、社会结构、社会政策、生态环境、房地产信息和文化媒介传播、高房价心理等宏观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与居住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社会环境如何经由“居住”这一中介变量形成全面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最后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因果分析和机制分析,以挖掘“社会环境—居住—不平等”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具体过程,彰显居住社会学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在政策运用上,则强调评估居住不平等带来的综合效应,从源头上制定综合性的社会政策以防止房地产阶级社会的产生。
其二,研究对象的扩展。“房地产阶级社会”概念启发我们不仅将住房作为居住不平等的研究对象,还应将土地、房地产市场等作为产生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居住不平等研究往往只关注住房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然而,“土地商品化”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实践可被视为导致现代社会住房不平等的前提和根源,也是现代性的另一种本质所在。诚如乔治(2010:7-8,306)提出著名的“进步与贫困”悖论一样,土地的私有和商品化是导致人类越进步、社会越贫困的症结所在,即“只要土地属于私人,不管人口增加,物质进步的后果必然迫使劳动者得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因为如果一个人能支配别人必须在其上劳动的土地,他就能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就是地租的不断增加——劳动为使用土地被迫支付的代价——夺走许多人正当获得的财富,使这些财富堆积到少数不劳而获者的手里”。因此,土地的公有化成为解决不平等的根本所在。然而,一个和塞勒尼(2010)强调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同样具有新古典社会学意义的问题出现了:在土地公有化的社会里也不同程度产生了居住不平等现象。因此,土地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成为令人着迷的领域,鼓励研究者面对非西方国家样本时,摒弃韦伯、马克思等古典社会学家预设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市场逻辑“非合即散”的二元式前提,积极发挥新古典社会学的想像力,探索转型社会中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和市场逻辑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于“土地”,使其成为决定社会不平等的中介变量。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在土地所有权国有化、使用权商品化的社会里,仍然存在住房不平等,个中必定存在围绕土地的国家再分配体系和市场运作逻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制,这也是居住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正如该书全面展示韩国房地产市场如何影响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样,“房地产市场”本身也应成为居住不平等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以往的房地产市场研究多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传统领域。由于其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产生一种封闭性较强的学科话语权力,使得社会学者较难涉足这一领域。但国内已有社会学者尝试研究房地产市场背后复杂的社会性逻辑。如李林艳(2008)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关系”如何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实际运行的内在逻辑,即“关系”作为一种微观的社会结构生成原则,在房地产市场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充当一种正式规则的转换机制;在房地产市场内部,则发挥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功能,从而深刻塑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形态。由此,我们可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遵循关系逻辑的话,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为类似韩国“政商学舆”各类力量相互交织的“土建国家复合体”的重要载体?这促使我们思考“关系化的房地产市场”与“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的机制和内容比起单独的“住房”或“土地”分化研究更具整体性和复杂性,因为“关系化的房地产市场”本身将“住房分配的关系化”和“土地使用权的关系化”等内容纳入其中,两者是前者的前提和有机组成部分,反过来又巩固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化,使其成为收入、权力和声望等因素共同作用并形塑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趋势的重要场域。因此,“关系化的房地产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更具新古典社会学的风格,成为居住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三,“房地产阶级社会”概念的反思性。该书的另一个启示在于,“某某社会”这类“诊断”病态社会式的社会学修辞法体现了审视社会运行和变迁逻辑合理性的反思性。例如,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表述方法本身是一种反思性视角,并非单纯描述充满风险的社会环境,而是从“风险”的角度反思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革,如职业模式的非正规化转换、传统家庭模式的衰落和个人关系的原子化等内容。“房地产阶级社会”用语的功能亦如此,并非强调一种“房地产决定论”,而是从“房地产阶级”的角度审视房地产阶级社会风险普遍化背后的社会结构固化风险,并深入分析房地产背后国家、市场、社会的复杂关系和作用机制。此外,日韩社会学者的研究中还出现很多反思东亚社会变迁的修辞概念,诸如说明日本和韩国盲目修建土木工程推动经济增长的“土建国家社会”;说明日本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下流社会”,以及强调日本处于“无血缘”、“无地缘”和“无社缘”等社会原子化倾向、独身人士居多的“无缘社会”等,都是把握东亚社会发展脉动的反思性视角。因此,对处于东亚现代化和市场转型双重语境中的中国来说,研究者更有必要借鉴东亚学者的此类社会学修辞方法,将“房地产”作为一种“内视镜”,反思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带来的社会效果,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兼具塞勒尼新古典社会学风格和东亚本土性的理论范式,为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理论的发展做出中国学界应有的贡献。
第二,该书在政策实践上的最大启示在于“国家回归”取向。即重视国家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上的道德责任。对于以具有公共性的“住房”和“土地”为基本要素的房地产市场,其本身并不完全适合于“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治理逻辑,需要更多政府的“回归”。例如,2013年9月引起争议的“以房养老”模式试点引发了民众对政府推卸基本养老的公共责任的担心。为此,民政部在媒体公开释疑,声称政府不会推卸基本养老责任,“住房养老”只是丰富养老模式的手段之一,是个人的自主行为。3但这种“国家的回归”并非权力垄断和粗放式的宏观调控,而是精细的“点面结合”式的政策取向。“点”强调准确把握社会各利益群体的阶层特点和具体需求,量身订制符合各阶层的房地产政策;“面”强调房地产政策的包容性和综合性。正如田毅鹏(2012)指出,东亚国家的包容性政策应重视一种强调共生思想和克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势关怀取向。因此,国家的回归并非国家权力的暴力介入,而是在社会各阶层共生的包容理念下尊重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身份,对其进行物质与社会功能上的综合性服务和保障。
然而,《房地产阶级社会》一书仍然存在一些缺憾,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1)房地产阶级意识。该书强调房地产资源的分配不平等导致房地产阶级的产生,但缺少对“阶级意识”这一中间环节的分析。阶级分析强调阶级的产生除了外在的制度和权力压迫之外,更需要劳动阶级内部在统一的集体认同基础上产生彰显主体性的阶级意识,即马克思强调的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同理,“阶级意识”也应是房地产阶级形成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应深入分析高房价的社会背景下,房地产资源如何培育无房阶级的集体意识,并探寻其背后的内在机制。(2)家庭因素与房地产阶级再生产。该书虽然将房产的数量作为划分房地产阶级的标准,却忽略了房产所有权的家庭形式对于阶级产生与再生产的重要作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对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各国来说可谓是意义非凡——不仅是在个人认知和行为方面具有“家族主义”倾向,而且在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社会组织结构以及资源分配逻辑上也有“泛家族主义”倾向。具体到房地产资源,在中日韩等东亚社会里,很多父母给子女买婚房(包括付首付),或是子女通过获赠和继承方式拥有房产,或是子女与父母同住,这些都是生活于高房价社会的应对策略。同时,也因家庭房产资源量的大小差异通过代际传递直接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定型化趋势。换言之,“房地产资源的代际传递”成为阶级或阶层再生产的新机制,也是综合体现权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高房价社会里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因此,房地产阶层的家庭结构与代际传递机制应引起研究者重视,它是东亚房地产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3)房地产阶级社会与东亚现代性。该书的另一特点在于将房地产阶级社会置于二战后韩国房地产发展史脉络下梳理高房价社会的历史逻辑。但作者似乎仍未触及东亚国家房地产异化发展的实质问题,即片面追求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异化问题。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对于东亚国家而言具有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对于国家来说,房地产行业是全球化和消费社会背景下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对于老百姓来说,房地产行业提供的公寓、洋房和别墅等住房形式可以让其拥有西式的生活方式。另外,东亚社会的安居乐业观念使得老百姓渴望拥有自己的产权房,固定的住房意味着有了安定的家,促使民众对房地产行业产生既爱又恨的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房地产背后的社会发展模式若继续追随西方式发展主义的话,房地产行业则会具有强烈的阶层分化性和社会分割性。换言之,非西方国家在推动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中往往采取强调工具理性、片面增长观、非共生性的发展主义模式。房地产市场在此类发展模式的催生下自然犹如洪水猛兽般肆掠整个社会。因此,当大家时下都在关注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微观政策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其背后宏观的社会发展模式。正如有学者积极倡导东亚“新发展主义”一样,东亚的现代性应是植根于和谐共生、民本思想等政治文化传统之上,并强调整体性与综合性的内生式发展逻辑(田毅鹏,2009;夏光,2005)。只有从源头上端正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理念,驱散发展幻想的迷雾,房地产发展的一系列困境才会迎刃而解,达到治标又治本的效果。
注释:
1.所谓“阶层定型化社会”是指一个社会的结构呈刚性的分布,阶层之间界限一旦形成,很难人为改变,人们也很难从一个阶层流动到另一个阶层,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呈现出一个刚性的结构。
2.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购买房屋的同时也要购买土地(宅基地),即房价既包括房屋的成本,也包括宅基地成本。
3.参见:魏铭言,2013-09-21,民政部:政府不会推卸养老责任,以房养老只是试点性举措,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3/0921/c64387-22981265.html;郑赫南,2013-09-20,“以房养老”引热议,专家称政府应承担最大养老责任,http://news.xinhuanet.com/yzyd/house/20130920/c_117436233.htm?prolongation=1。
| [] |
边燕杰. 2005.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3): 82-98.
|
| [] |
李强. 2009. 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
江苏社会科学(4): 42-53.
|
| [] |
李林艳. 2008. 关系、权力与市场——中国房地产业的社会学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
刘祖云, 毛小平. 2012. 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2): 94-109.
|
| [] |
毛小平. 2014. 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
社会, 34(2): 118-139.
|
| [] |
乔治, 亨利. 2010. 进步与贫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 |
塞勒尼, 伊万. 2010. 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
孙金楼. 1983. 住宅社会学研究课题之我见.
社会, 3(4): 36.
|
| [] |
孙金楼. 1987. 当前住宅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社会, 7(1): 32-33.
|
| [] |
孙金楼. 1990. 我国住宅社会学研究综述.
社会学研究(4): 73-77.
|
| [] |
孙立平. 2008. 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新远见(11): 121-128.
|
| [] |
孙洛龟. 2012. 房地产阶级社会[M]. 芦恒,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 [] |
田毅鹏. 2009. 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
田毅鹏. 2012. 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
社会科学(1): 75-80.
|
| [] |
夏光. 2005. 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 从文化的角度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 |
张仙桥. 1995. 住宅社会学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学研究(1): 13-19.
|
| [] |
Liu Zuyun and Hu Rong. 2010. "Urban Housing Stratification:An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06 Data.
社会, 30(5): 164-192.
|
| [] |
Saunders Peter. 1984. "Beyond Housing Class: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Means of Consum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8: 202-227.
|
| [] |
Rex, John and Robert Moore. 1967.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A Study of Sparkbroo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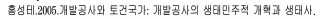
|
 2014, Vol. 34
2014, Vol.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