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家庭暴力已成为危害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是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关注与重点治理的问题。夫妻间或亲密伴侣关系暴力不仅使受虐者权益受到不良侵害,也会对长期暴露在暴力环境中的儿童(目睹儿童)产生严重后果。一些儿童甚至会通过观察、模仿、强化、合理化来习得家暴行为,在成年后出现因原生家庭暴力行为而影响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倾向,形成家庭暴力代际传递。
近年来,在专家、学者不断倡导下,我国对家庭暴力及其防治有了更多认识。然而,目前国内对家庭暴力研究主要针对施暴者与受暴者,对目睹儿童这一群体的理论探讨、学术研究不多,特别对一些隐蔽性的行为、目睹儿童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了解不深,缺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因此,笔者对当前国内外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针对家庭暴力对目睹儿童的影响、目睹儿童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等关注点展开回顾与综述,以期为我国家庭暴力目睹儿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并在目睹儿童保护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概念界定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特别是夫妻间或亲密伴侣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主要指现任或前任伴侣对其采取的身体、心理、性和其他具有侵害性的控制行为。[1]自1973年“家庭暴力”一词被提及后,其严峻性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持续性议题。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世界上约有400—900万人曾遭受家暴,近17亿人(全球人口的60%)存在被家庭暴力威胁的可能。[2]由于家暴行为的隐蔽性等特征,一些受暴者并未上报真实情况,实际发生的案例数量可能远超这个数字。
(一) 家庭暴力
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并赋予其内涵。除了针对妇女暴力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针对性别差异的《妇女公约》外,国际上通常使用1993年联合国对家庭暴力的明确定义进行阐述,即家庭暴力是在家庭中发生的任何针对身体、心理或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对家族成员的殴打、性虐待、婚内强奸、生殖器切割、其他剥削性举止等夫妻间、非配偶间的暴力行为。[3]其后又不断对家庭暴力的内涵进行扩展,将精神暴力、经济暴力、目睹暴力、同性伴侣间的暴力等纳入家庭暴力范畴中。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已有学者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并对家庭暴力的涵义进行界定,如马原介绍家庭暴力是损害家庭成员身体、心理、性方面的强暴行为。[4]随后,国内关于家庭暴力定义的探讨开始涌现。如张亚林认为,家庭暴力形式涉及多个方面,除了殴打、折磨、拘禁、残害等身体攻击,还包括心理层面及性相关的伤害。[5]
(二) 目睹儿童
国外学者对目睹儿童的界定略有不同。早期一般从字面意义来确定目睹儿童的定义,认为他们是家庭暴力的直接观察者(observer)或目击者(wit-ness)。[6]而后Holden在自己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将目睹儿童限定范围扩展至“暴露在家庭暴力环境中的儿童”(exposure)。[7]Abbassi等也将定义阐述为曾目睹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威胁、殴打、施暴等侵害性行为,或听到暴力发生声音而未直接看到行为发生,或仅看到暴力发生的结果(如伤痕),而自己未受到直接暴力伤害的儿童都可被称为“目睹儿童”。[8]在我国,家庭暴力环境中以儿童为对象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直接受虐群体上,对于目睹儿童这一隐形群体鲜有关注与保护,相关文献资料也较少。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是较早开始探讨该问题的机构,机构研究员在2006年时已提出目睹暴力属于暴力侵害的一种,也会对儿童造成不良影响且容易被社会忽视。[9]其他学者虽然对儿童目睹家庭成员间暴力行为有所介绍,但并未直接对“目睹儿童”进行明确定义。
全球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目睹儿童数量庞大,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调查,我国每年至少有4 000万未成年子女曾在家庭中目睹暴力行为发生。[10]
二、国外对家庭暴力中目睹儿童代际传递的研究现状综述(一) 国外对家庭暴力的研究
笔者通过查阅已出版专著和论文集、翻阅互联网期刊资料库如google scholar、与国(境)外高校研究学者探讨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文献资料。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后,笔者对国外家庭暴力的相关研究有了基本认识。
1. 家庭暴力的成因
国外学者对家庭暴力的成因划分得较为细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生理学、心理学为取向的理论。Buzawa、Gelles和Loseke主要从医学角度对家庭暴力进行研究,认为施暴者自身的荷尔蒙失调、心理缺陷或精神疾病是导致暴力的主要原因。[11-12]二是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后期家庭暴力防治领域的主流观点,如Renvoize认为,家庭结构与交流模式可能引发家庭暴力的发生;[13]而Gover团队、Abbassi和Aslinia等人则倾向于暴力循环理论(即“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作用。[8][14]三是社会文化与环境理论。一些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某些奉行大男子主义文化的国家或地区容易认可以暴力行为的方式解决家庭矛盾或问题,女性家庭成员在受虐过程中也较少产生“反抗”念头。[15]此外,家庭生活条件与状态也是影响家庭暴力产生的因素,比如低文化水平、缺乏营养、高抑郁程度、低社会经济状态(SES)、失业、低龄父母等都会增加家庭暴力产生的可能性。[15-19]
2. 家庭暴力的影响
家庭暴力对受暴者影响巨大,除了会严重损害受暴者的身体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等反应,[20-21]还会对家庭暴力受虐者产生更深远的影响。Beck等在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进行访谈时发现,她们不仅产生了羞愧、恐惧的不适感,还出现了闪回(重新体验)、否认(情绪低落)、警惕(焦虑状态)等症状,存在应激性创伤后精神障碍(PTSD)的可能。[22]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还会导致酒精或药物滥用的情况发生,如不同学者在几次调查中均发现有极高比例的受虐妇女在烟草、酒精、药物等各类测试中呈现阳性反应。[23-25]
对于施暴者来说,目前并无系统性研究对其所受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有学者认为家暴行为对施暴者本身也产生影响。如Peled和Gil发现施暴者会出现态度强势、霸道、极少关注其他家庭成员如儿童或老人基本需要的情况。[26]
家庭暴力不仅与施暴者和受暴者有着紧密联系,还会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特别是目睹儿童产生深远影响。家庭是儿童学习、成长的第一空间,儿童在家庭环境中所获得的认知与行为都对其成年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二) 家庭暴力对目睹儿童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于未成年人目睹家庭暴力的研究较早,针对这一群体所受伤害的应对方案也相对完善。Kolbo及其团队早在1996年就开始对家庭暴力中的目睹儿童进行跟踪研究,结果发现,即使没有直接受到暴力伤害,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儿童也很容易出现情绪、行为等各方面问题,对其个人成长与社会融入产生不可预估的危害,并且这种影响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慢慢显现出来。[27]
国际临床调查发现儿童在目睹家庭暴力之后有很大机会出现应激性创伤后精神障碍(PTSD),比如出现暴食症、抑郁症等症状,对其身心各方面造成危害。[28-30]部分目睹儿童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排解压力或直接对目睹现象进行反击,而是更倾向于将家庭暴力行为带来的影响与痛苦释放在学校等他们更有控制力的环境中。Lodge在其2014年的一次调查报告中表明,相较没有目睹过父母之间家庭暴力的儿童而言,成长在暴力环境中的孩子更容易在学校、社区等地方模仿或展示他们所习得的攻击性行为,例如校园霸凌、顶撞师长,或产生一些逃避行为,如翘课、习惯性请假、消极学习等。[31]一些研究人员还发现,施暴者的家暴行为与其儿童时期的暴力经验有密切关联。Corrado等人对大量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和个人经历进行分析后发现,多数人在童年时期曾频繁目击父母间暴力行为。[32]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暴力行为对不同性别的目睹儿童所起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这样的影响通常反映在他们成年后的人生经历中。Leinonen等人认为,男孩容易出现反社会性攻击、过度活跃、分心走神等外显性行为,而焦虑、惊恐、回避等内化性行为较常体现在女孩身上。[33]在对一些家庭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后发现,男孩、女孩是否出现既定反应(即男孩的外显性行为与女孩的内化性行为)往往和家暴行为施暴者的性别有关。Stith于2000年在其报告中指出:若施暴者和受虐者分别为男性和女性,则该家庭中的目睹男童有很大比例会在其成年后建立的核心家庭中展示暴力行为;曾在童年时期目睹母亲被父亲家暴的女孩则更有可能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人。[34]这意味着家庭暴力的目睹儿童可能在观察到同性别家长的行为方式并重复学习后,在新的环境中进行模仿与展示,造成新的家庭暴力。
(三) 家庭暴力中目睹儿童的代际传递
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是目睹儿童习得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Black及其团队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孩子若长期生长在暴力环境下,容易出现习得性家暴行为,形成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interge- nerational transmission,IGT),并在其成年后常出现因原生家庭中的暴力行为而影响自己核心家庭的倾向。[35]观察学习在整个童年时期都是至关重要的学习方式,也是代际传递和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价值。班杜拉(Bandura)在其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他们的许多行为是在观察中习得发生的”,并通过注意、保持、动作重复、动机这四个阶段在社会情境中学习社会行为。[36]如果一种行为的发生所带来的积极结果(奖励)大于负面影响(惩罚),他们就会更容易在下一次相同的情境中对该行为进行模仿和重复。美国刑事司法专家Briggs在谈论家庭暴力问题时表示,长期暴露在家暴环境中的儿童会产生“暴力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合理方式”的错误认知,因为他们并未从家庭日常中学习到解决冲突的其他方法。[37]
许多研究已揭示家庭暴力会导致目睹儿童出现暴力的代际传递。Abbassi,Gover和Yoshihama等一批学者通过大量案例研究与数据分析后认为,目睹儿童在成年后可能会对家暴行为产生模仿或重复的行为。研究者对曾遭受暴力的家庭进行跟踪研究后发现,在家庭暴力中耳濡目染成长的儿童与参照组对比而言,更易在施暴者或受暴者处习得相关行为。[8][14][38]Ehrensaft在一个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儿童阶段曾看到或听到父母家暴发生的个体,其成年后实施暴力行为的比率是对照组的3倍。[28]
Mc Clennen,Hamberger和Potente等研究人员对家庭暴力中目睹儿童代际传递行为的介入模式秉持相同的观点,即在家庭亲密关系间暴力行为发生之后应立即采取干预行动,制止家暴行为的继续发生,保护受害人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基本权益,这也是从根本上改变目睹儿童所处环境的途径。[2][39]一些学者认为,应推动与儿童心理学专家、社会工作者、精神科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合作,对潜在的目睹儿童进行风险评估与干预,通过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儿童成长小组①、与父母单方或双方的亲子交流活动等,建立理性的家庭关系处理观念,改善目睹儿童心理情绪与认知行为。[8][39]
三、我国国内关于家庭暴力中目睹儿童代际传递的研究现状国内对家庭暴力的研究虽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主要是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家庭暴力案例进行回顾,且是针对法律法条的研究。2000年以后,学界对家庭暴力问题开始深入研究,对其成因、理论、影响因素及解决方法也有了更为全面的剖析。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平台的相关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2000年至今,以“家庭暴力”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共16 076篇,其中大量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政治、法律法制、司法行政开展,而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的文献约有1 500篇。其中,与“目睹儿童”相关的文章仅31篇,而以“目睹儿童代际传递”为主题的研究不到5篇。②从数量上来看,虽然我国近几年对家庭暴力干预的研究呈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对于家庭暴力环境中目睹儿童及其代际传递现象的分析还很欠缺,其研究空间还很大。
(一) 国内对家庭暴力的研究
1. 家庭暴力的成因
国内对家庭暴力产生因素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以个体为取向。比如张亚林、欧竹青等从心理学理论出发,认为施暴者缺少自我控制能力,存在心理或情绪问题。[10][40]第二,以家庭整体为单位。如王淑婕、刘衍玲等人从家庭结构理论、暴力循环理论(代际传递)进行分析。[41-42]第三,从性别理论及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家庭暴力的成因进行剖析。在社会学、社会工作领域对家庭暴力研究较多的刘梦认为,家庭暴力的发生是由现代女性平等观念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失范”情形代入婚姻导致的。[43]佟新在对34对受虐妇女的深入访谈后发现,家庭暴力产生的本质原因是施暴者与受暴者两性关系之间权利的不平等导致的身心、经济方面的能力限制。[44]肖凌燕、王凤仙则认为,男权文化等社会文化标准、女性自身传统观念的束缚等原因是女性家庭成员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原因。[45-46]李春斌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在具体的司法援引和实践中功能弱化,难以保护女性受害者的权益,过低的犯罪代价不能对女性起到强有力的保护作用。[47]但也有一些人通过研究后认为,施暴者与非施暴者的性别不是区分施暴与否的关键因素。如曹玉萍等人认为,暴力行为与性别无关,男性也可能经常受到殴打。[48]
2. 家庭暴力的影响
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受暴者在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均产生不良影响。仲鑫认为,家暴行为容易造成受暴者的身体创伤,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残疾甚至危害生命的情况,[49]如2009年董珊珊家暴致死等触目惊心的案件。郭素芳在对妇女、儿童进行实证调查时发现,长期生活在暴力行为和冷暴力影响下的妇女可能出现抑郁、孤僻等心理健康问题。[50]在我国西部农村某地的一项调查发现,过去1年中遭受过暴力行为的妇女出现自杀想法的可能性是对照组的近5倍。[51]家庭暴力作为影响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夫妻关系和谐,也可能出现受暴者“以暴制暴”的极端反抗行为,[52]2015年泸州女子不堪家暴杀夫案就体现了这一点。
若受暴者为儿童,家庭暴力也会产生许多深远影响。关颖在对全国2 700多名未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经常受到父母家庭暴力行为的儿童易出现自卑、冷酷、暴躁等心理、性格问题,或加剧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盗窃、结交不良玩伴等行为的发生,甚至对家庭、社会产生报复、仇恨的心理。[53]
(二) 家庭暴力对目睹儿童的影响
我国学者对未遭受家庭暴力直接侵害的“目睹儿童”也有一些研究。第一,从生理学、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将两组儿童进行对照后发现,小时候目睹家暴行为会刺激儿童大脑的杏仁核与前脑岛,与同龄人相比,目睹儿童的右脑控制视觉感官的部分萎缩了近20%。[54]张亚林等人则认为,长期生活在暴力环境中的儿童,无论是否直接遭受暴力行为,都可能损伤其认知系统。[10]刘秀琳则发现,目睹儿童可能会出现胃痛、气喘、尿床、暴饮暴食和睡眠问题。[55]第二,从认知行为视角进行研究。苏英团队在湖南、内蒙两地的问卷调查中发现,目睹父母间冲突的儿童更容易产生违纪行为或反社会行为,在情绪问题、矛盾问题处理上也会受到影响。比如目睹父母间的家庭暴力不仅对亲密关系暴力行为合理化进行解释,更通过此种行为反复的强化作用提供榜样行为。[56]第三,从心理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陈晶琦等人通过调查发现,目睹儿童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和其他精神病症状。[9]关雨琪在对小P个案进行研究时了解到,目睹儿童还会有无力感、愧疚感、罪恶感等精神创伤的迹象。[57]
(三) 家庭暴力中目睹儿童的代际传递
刘衍玲认为,家庭暴力存在三种类别的代际传递效应,其分别是夫妻间、亲子间、夫妻与亲子间暴力共存的代际传递。而夫妻间暴力的代际传递主要是通过儿童目睹其父母的夫妻间家暴并在将暴力行为传递给成年后新生代家庭这一方式完成的。[42]
内地目前对儿童时期受虐经历与成年后施暴行为的耦合效应已有一定认识。从20世纪末开始,已有大量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成年后的施暴行为可能是其对童年受创经历进行模仿、习得、固化家庭暴力模式的结果。[41][44]但针对“目睹儿童”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效应的研究还不多。王淑婕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分析,认为家庭是学习暴力行为的“隐形课堂”,长期目睹父母间的施暴行为会使儿童倾向于成长为诉诸暴力解决问题的个体。[41]柳娜等人则通过多种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儿童时期目睹家庭暴力的人更容易在成年后成为严重躯体施暴者。[58]
香港地区对家暴问题的关注和干预较早,关于“目睹儿童”这一群体的家暴行为代际传递研究也较为前沿。[59]2014年,学者Chan在对内地18 341个代表性个案进行研究时发现,童年时期曾目睹过双亲暴力、老年虐待、姻亲冲突等家庭暴力举止的成年人,较未经历过暴力环境的人而言,更易出现多种暴力行为。[29]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在最新一次香港本地的实证研究报告中指出,目睹家庭暴力与直接受到家暴伤害,都可能增加成年后夫妻间或其他亲密伴侣间的暴力行为,二者的比例基本一致。[30]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直接受到身体伤害的儿童,其身心创伤更多的观念有所出入。
四、述评与展望(一) 国内外研究成果评价
1.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学者对目睹儿童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问题研究,主要通过对家庭暴力、目睹儿童、代际传递各个领域的关系进行宏观审视,以目睹儿童为落脚点对其内涵、影响、干预等多层面进行微观分析,并经过大量理论探索和多种实证方法分析,对目睹儿童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这些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
(1) 研究方法多样。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案例归纳、对照组实验、常年跟踪调查等方式进行研究,不但有数据分析成果,也为目睹儿童后期干预的实效性研究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可量化问卷及标准。
(2) 研究群体全面。国外学者较早认识到除了要关注家庭暴力的受暴者,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暴露在暴力环境中的其他家庭成员(如目睹儿童)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因此,可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也较多。
(3) 理论思辨、成因分析、介入模式三位一体的系统性研究。大量资料以成熟的各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并以此为框架进行分析,也简单地讨论了一些有价值的干预手段和介入模式,对改善目睹儿童生活环境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2.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近年来,由于政府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推动和公民热情参与,我国家庭暴力防治领域的发展较快,对于家庭暴力问题的干预、受暴群体的保护也有了更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成因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二是对家庭暴力的影响、干预措施的分析更加深入;三是开始注意到目睹儿童这一隐形群体。
然而,国内研究虽然在家庭暴力内涵及其防治上从多个角度有较多研究,但是综合性文献回顾较少,目前仅有黄列、陈雯、陆瑾等分别从法律范围、内涵界定、家暴成因及影响等角度进行研究,没有相对系统性、全面性的综述可以参考。[60-62]同时,对目睹儿童这一群体的关注还不多,特别对目睹儿童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相关研究还很缺乏,专业评估与介入的阐述也相对不足。目前仅有王淑婕、柳娜等人对其形式特点、文化背景进行简单介绍,其研究报告鲜有关于介入阶段从施暴者、受暴者、目睹儿童等其他家庭成员多方面进行介入治疗模式的说明。[41][58]201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也未将未成年人目睹家暴行为纳入家暴防治的法律范畴。[63]
(二) 未来研究方向与建议
1. 强化不同暴力类型的代际传递理论分析
现有研究主要以身体暴力这一暴力类型进行具体分析。还有精神暴力、性暴力、非配偶间的家庭暴力等暴力类型,儿童在目睹这些攻击行为后是否存在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效应?如果存在,其代际传递机制与理论解释是否与一般的身体暴力相同?同时,现有研究主要以女性受暴者为对象进行分析。当前,精神暴力、性暴力案例中男性受暴者的数量不断增多,强化对这些类型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有助于对整体机制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
2. 探索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介入模式
目前国内外针对目睹儿童这一群体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成因、影响因素等方面,很少对评估与介入手段进行相关研究。一些国外学者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但是相对简单,大多用一句话(如使用认识行为治疗方法、小组活动等方式)笼统带过,并未深入探讨具体的操作模式及方法。对于这一情况,可以从暴力行为的施暴者、受暴者、目睹儿童及其他家庭成员(如目睹老人)等角度设计针对性方案,为临床治疗及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3. 推进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本土化研究
关于目睹儿童的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国内研究大多以核心家庭为主。但由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不同,我国家庭结构中常包含更为复杂的三代或多代姻亲关系,如婆媳、兄弟、祖孙等。这些群体或关系在代际传递中起到什么作用?对暴露在暴力行为下的目睹儿童会起到何种影响?我国本土文化或价值思想对这一领域是否存在特定影响?加强这些方面的本土化研究,可以对我国社会文化下的家庭暴力中目睹儿童代际传递有更深入、更全面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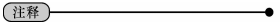
① 儿童成长小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小组成员全为目睹儿童的自助互助小组;另一种则是目睹儿童与一般儿童各占一半比例,在分享成长的过程中目睹儿童可以观察并学习一般儿童的做法,以促进他们改变思维认知并习得正确的家庭问题处理方式。
② 笔者2017年4月在中国知网上查询统计获得相关数据。
| [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response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non-intimate partner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EB/OL]. [2017-04-20].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85239/1/9789241564625_eng.pdf. |
| [2] | M CLENNEN J, M CLENNEN J C. Work and family violence: theories,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M]. Berlin: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LLC, 2010: 28. |
| [3] |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 December 1993), 85th plenary sess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EB/OL]. [2017-04-20].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8/a48r104.htm. |
| [4] | 马原. 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 111-112. |
| [5] | 张亚林. 论家庭暴力[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5): 385-387. |
| [6] | HOLDEN G W, RITCHUE K L. Linking extreme marital discord, child rearing,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Evidence from battered women[J]. Child development, 1991 (62): 311-327. |
| [7] | HOLDEN G W. Children 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 abuse: terminology and taxonomy[J].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03 (8): 9. |
| [8] | ABBASSI A, ASLINIA S D. Family violence, trauma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y[J].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prac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2010(1): 16-27. |
| [9] | 陈晶琦, 梁艺怀, DUNNE M P, 等. 青少年童年期目睹暴力经历回顾性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4): 234-237. |
| [10] | 张亚林, 曹玉萍. 家庭暴力现状及干预[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35. |
| [11] | BUZAWA E S, BUZAWA C G. Domestic violence: th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M].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5. |
| [12] | GELLES R, LOSEKE L. Current controversies on family violenc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3: 5. |
| [13] | RENVOIZE J. Web of violence: a study of violence in the family[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5. |
| [14] | GOVER A, KAUKINEN C, FOX K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ce in the family of origin and dating viol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08 (23): 1667-1693. |
| [15] | ACIERNO R, RESNICK H S, KILPATRICK D G. Health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prevalence rates, case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factors for sexual assault, physical assault, and domestic violence in men and women[J]. Behavioral medicine, 1997(23): 53-64. |
| [16] | FIELD C A, CAETANO R. Ethnic difference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he US general population: the role of alcohol us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J].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2004 (5): 303-317. |
| [17] | SCHUMACHER J A, SLEP A M S, HEYMAN R E. Risk factors for male-to-female partner psychological abuse[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1 (6): 255-268. |
| [18] | BROWNRIDGE D A, HAALI S S. Double jeopardy? Violence against immigrant women in Canada[J]. Violence and victims, 2002(17): 455-471. |
| [19] | DAIGNEAULT I, HEBERT M, MCDUFF P. Men’s and women’s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victimization in adult partner relationships: A study of risk factors[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09(33): 638-647. |
| [20] | CAMPBELL J C. Health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The lancet, 2002( 359): 1331-1336. |
| [21] | LEUNG T W, LEUNG W C, LAM Y, et al. Quality of life of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 2005(90): 258-262. |
| [22] | BECK J G, MCNIFF J, CLAPP J D, et al. Exploring negative emotion in women experienc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hame, guilt, and PTSD[J]. Behavior therapy, 2011 (42): 740-750. |
| [23] | HANKIN A, SMITH L S, DAUGHERTY J,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risk of substance abuse and depression among African-American women in an urban emergency department[J]. Wester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10 (11): 252-256. |
| [24] | HELLER N R, GITTERMAN A.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problems: a social work perspective[M]. Oxon: Routledge, 2011: 5. |
| [25] | YAN E, CHAN K 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older Chinese couples in Hong Kong[J].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012(24): 1437-1446. |
| [26] | PELED E, GIL I B. The mothering perceptions of women abused by their partner[J].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11(4): 457-479. |
| [27] | KOLBO J, BLAKELY E H, ENGLEMAN D. 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 a review of empirical literature[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996(2): 281-293. |
| [28] | EHRENSAFT M K, COHEN P, BROWN J,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tner violence: A 20-year prospective study[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3(4): 741-753. |
| [29] | CHAN K L. Child victims and poly-victims in China: Are they more at-risk of family violence? [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4(38): 1832-1839. |
| [30] | YAN E, KARATZIAS T. Childhood abuse and curren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population study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6(38): 1-19. |
| [31] | LODGE J. Children who bully at school[J]. Australian government paper, 2014(27): 25-38. |
| [32] | CORRADO R R, ROESCH R, HART S D. Multi-problem violent youth: a foundation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needs, interventions, and outcomes[M]. Amsterdam, NLD: IOS Press, 2001: 5. |
| [33] | LEINONEN J A, SOLANTAUS T S, PUNAMAEKI R L. Parental mental health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the quality of marital interaction and parenting as mediating factors[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 allied disciplines, 2003(2), 227-241. |
| [34] | STITH S M, ROSEN K H, MIDDLETON K A, et al.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pouse abuse: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000(3): 640-654. |
| [35] | BLACK D S, SUSSMAN S, UNGER J B. A Further look 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witnessing inter-parental violence in emerging adulthood[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2009(6): 1022-1042. |
| [36] | 班杜拉.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社会学习理论[M].陈欣银, 李伯黍,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5. |
| [37] | BRIGGS S, FRIEDMAN J. Criminology for dummies[M].L A.: Wiley Publishing, Inc, 2009: 5. |
| [38] | YOSHIHAMA M, HOEEOCKS J.Risk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ol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sexual initiation in women in Japan[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0(32): 28-37. |
| [39] | HAMBERGER L K, POTENTE T. Counseling heterosexual women arrested for domestic violenc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J]. Violence and victims, 1994(2): 125-137. |
| [40] | 欧竹青, 席春玲. 对家庭暴力的心理学视角分析[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3(12): 28-35. |
| [41] | 王淑婕. 论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J]. 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 2006(5-6): 85-86. |
| [42] | 刘衍玲, 廖方新, 郑凯, 等.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 类型、理论和影响因素[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201-209. |
| [43] | 刘梦. 中国婚姻暴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05. |
| [44] | 佟新. 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0(1): 102-111. |
| [45] | 肖凌燕. 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原因分析及心理治疗[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132-135. |
| [46] | 王凤仙. 反抗与妥协——家庭暴力受害者个案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01(5): 18-25. |
| [47] | 李春斌. 男性作为家庭暴力受害人问题研究[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1(4): 18-21. |
| [48] | 曹玉萍, 张亚林, 杨世昌, 等. 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关因素的比较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1): 28-30. |
| [49] | 仲鑫. 中国家庭暴力研究评述[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62-66. |
| [50] | 郭素芳.产后抑郁与产后家庭暴力[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9): 629-631. |
| [51] | 高燕秋, JACKA T. 西部农村地区家庭暴力发生情况及对妇女精神健康的影响[J].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2(3): 379-386. |
| [52] | 王俊, 王东萌. 家庭暴力中女性以暴制暴的犯罪成因[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91-96. |
| [53] | 关颖. 家庭暴力对儿童的伤害及其社会干预[J]. 当代青年研究, 2006(5): 22-27. |
| [54] | 蓝建中. 孩子常目睹家庭暴力会使大脑视觉皮层萎缩[EB/OL]. (2010-03-04).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0-03/04/content_13096785.htm. |
| [55] | 刘秀琳, 曾迎新. 家庭暴力对目睹儿童的影响及其处遇策略之探讨[A/OL]. [2017-04-20]. http://edu.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Detail/7638276. |
| [56] | 苏英, 洪炜, 崔轶. 目睹父母间冲突与儿童行为问题[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3): 486-489. |
| [57] | 关雨琪. 家庭暴力目睹儿童的社会工作干预——对小P个案的介入和思考[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5. |
| [58] | 柳娜, 陈琛, 曹玉萍, 等. 家庭暴力严重躯体时报行为的代际传递——目睹家庭暴力[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1): 84-87. |
| [59] | 王玲, 吴清禄, 蔡兆欣. 香港亲密伴侣暴力危机评估与控制的实践经验和启示[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6(6): 19-27. |
| [60] | 黄列. 家庭暴力: 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上)[J]. 环球法律评论, 2002(123): 104-114. |
| [61] | 陈雯. 家庭暴力研究: 回顾与前瞻[J]. 学习与实践, 2008(8): 136-143. |
| [62] | 陆瑾. 国内家庭暴力研究进展[J]. 黑河学刊, 2016(1): 138-139. |
| [63]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EB/OL]. (2015-12-28).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5-12/28/content_1957457.htm. |
 2018, Vol. 18
2018, Vol.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