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界对话语中评价现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Martin & White(2005)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提出了评价理论,开始了对语篇评价资源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研究[1]7。目前,新闻语篇评价已经成为评价研究中的主领域之一,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王振华论述了“硬新闻”中的态度[2],刘世铸、韩金龙探讨了新闻语篇的评价系统[3],Bednarek系统分析了报纸媒介中的评价资源[4],王天华探讨了新闻语篇中的隐性评价意义[5]。
在这些研究中,评价对象一般限于文字,对其他非语言符号的评价资源关注较少。随着现代网络媒体的兴起,要对新闻语篇的评价资源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就必须构建一个多模态语篇评价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评价理论。多模态评价已经成为有待研究者去开拓的新空间[6]。在新闻媒体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的今天,配有图片的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主流,图文互动的评价模式已经成型。而学界对于图像评价功能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但作为一种评价资源,它们的重要性丝毫不比文字部分低。
鉴于学界对新闻语篇的多模态评价研究不够系统的现状,本研究试图在这一领域作出尝试,将评价理论和视觉语法相融合,探索图文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并运用该评价模型来对比分析中西方媒体对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的报道。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媒体《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新华网》和《环球时报》关于巴黎恐袭的图文报道各10篇(2015年11月13日至18日),总共40篇报道。为了便于新闻图片的分析和采集,本文的语料均源于这些媒体的官方网站。
1 多模态新闻语篇的图像评价意义要构建新闻语篇的图文互动评价模式,首先需要揭示图像的评价功能,因为它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一种多模态评价资源,新闻图片的优势是简洁直观和辨识度高,人们往往在阅读文章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图片,第一印象已经形成。因此图片和新闻标题一样,在新闻语篇的评价意义构建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受众普遍认为图片客观真实,使其具有了很强的说服力,但图像所传达的评价意义往往不是外显的(图片中配有说明文字的除外),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应该探究隐含在图像中的评价意义,提高受众的批判性阅读能力。正因为图像具有客观真实的表象,报道者可以更为有效地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影响受众的认知和意识形态,引导社会的舆论走向。图片既可以单独表达观点,也可以和文字互相印证、相互补充,增强语篇整体的劝服效果。
Martin & White提出的评价理论主要是针对文字语篇,即:显性的词汇和语法评价资源[1]3。其实,语篇中评价无处不在,图像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要揭示图像的评价意义,首先需要了解图像的意义表达模式,学界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外学者如Kress & Van Leeuwen把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到非语言符号的解释中[7]41,将各类意义的图像特征和实现方式进行了细化,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分析视觉图像的语法框架;Martinec & Salway则系统论述了新旧媒体中的图文关系[8]。国内学者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如朱永生和张徳禄探讨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9-10],李战子、陆丹云进行了社会符号的多模态化研究[11]。这些研究为多模态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也为揭示多模态语篇的评价意义创造了条件。
为了进一步扩展评价的研究对象,可以把国外学者Kress & 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分析融入到评价理论中去,从而构建图片评价的分析模型。图像也像语言一样,能同时实现3种元功能:(1)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对应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2)互动意义(interactional meaning)对应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3)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对应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7]44。
1.1 视觉语法与图像的表意模式在视觉语法中,任何符号模态都能再现现实世界中的物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觉符号也不例外,这被称为符号的再现意义。根据图像的不同属性,它们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叙事图像,另一类称为概念图像,所以再现意义可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
Kress & Van Leeuwen用参与者(participants)来指代在视觉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物体或元素。另外,他们认为在任何一个符号行为中,都存在着两种“参与者”:互动参与者(interactive participants)和再现参与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7]47。当参与者被一个矢量(vector)连接起来之后,如一条斜线或者视线,他们就会被认为向对方做了某些事情,这种带有矢量的图像模型被称为是叙事图像。而概念再现是不带有矢量的,它们主要是用来表达一种“命题”意义,表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变化过程等。
互动意义类似于功能语法中的人际功能,指图像创作者、图像中的事物和图像浏览者之间的交互关系。Kress & Van Leeuwen主要划分了三种互动意义:接触(contact)、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和态度(attitude)[7]118。接触是指通过视觉交流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们认为每一个图像都可以满足两个图像行为(image act):索取(demand)和提供(offer)。当图像索取时,再现参与者会使用矢量把参与者和浏览者连接起来,如:直视图像浏览者。当图像提供时,再现参与者通常不凝视浏览者,而主要提供信息,科技图表、地图等属于这个类别。视觉语法主要区分了三类社会距离:近距离(close up)、中距离(medium shot)和远距离(long shot)。近距离一般只显示人物的头和肩部;中距离一般显示人物膝盖以上的部分;而在长距离中,人物一般占据框架内的一半高度。态度主要表达的是一种观点,而在视觉交流中态度主要是通过视角来表达的。视角的选择能够表现出参与者与互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视觉语法中,前视视角表示参与和融入,斜视视角表示疏远,俯视视角突出浏览者的权力,平视视角表示平等,仰视视角突出再现参与者的权力和表述权[7]149。
视觉语法中的构图意义对应于功能语法中的语篇意义,指的是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的表达元素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的构造或布局方式。图像的构图意义主要是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来实现的: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salience)和框架(framing)[7]176。信息值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构图中,各种不同要素的安放和布置方式能够提供特定的信息值。显著性指的是图像中某种元素被突出安排,这种强化和凸显效果可以通过颜色、焦点、视角等手段来实现。框架是通过线条等框选工具来隔开或连接不同的图像元素。
另一方面,在充分了解了图像的表意机制后,就可以结合评价理论来进一步发掘其评价意义。其实,Martin & Rose不仅系统地论述了文字符号中的评价意义,还将他们的分析扩展到了其他视觉符号,勾勒出了图像模态的评价模式[12],只是这一部分的论述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几年,多模态话语分析与语篇评价的结合逐渐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陈瑜敏论述了奥运电视公益广告多模态评价意义[13],冯德正、亓玉杰探讨了多模态语篇中态度意义的建构[14],石春煦、王振华揭示了多模态历史教科书中的评价语义[15]。
1.2 评价理论与语篇的评价模式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是语篇评价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和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它主要关注语篇表现出来的各种态度、倾向和观点。根据Martin & White的论述,语篇的评价可以分为三个子系统: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1]35。
态度是评价理论的核心部分,它主要指说话者对人的品行、事件或现象等所作的主观判断和评注。态度可进一步细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子系统。情感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情绪反应,主要涉及主观心理感受,如快乐、恐惧、悲伤等。情感意义可以分为反应型(reactive)和欲望型(desirable)。前者属于现实型情感,主要关注当下,如快乐/悲伤、安全/不安全等;而后者属于非现实型情感,主要针对将来,如恐惧和欲望等。
判断是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被评价者的道德品行作出价值评判,如强大、愚蠢、聪明等。判断所涉及的范畴相当广泛,涵盖了社会、道德、法律等层面的价值评判。判断分为两个方面:社会评判(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 sanction)。社会评判与人的行为规范、才干、韧性等相关;社会约束则与是否真实诚信,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有关,主要涉及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评价。
鉴赏主要是指对外部事物和过程进行的评价,包括抽象事件、自然事物以及语篇本身。它可以分为三个次系统: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valuation)。反应评价主要涉及过程的影响或质量。构成主要针对语篇结构的复杂性或细节进行评价。价值则是根据事件的社会价值对过程进行评价。
1.3 文本分析与新闻图片评价意义的表达笔者借鉴视觉语法和评价理论,选取中西方媒体关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来进行对比研究,其中图 1和图 2来源于西方媒体,图 3和图 4来源于中方媒体。分析步骤是先运用视觉语法解析出新闻图片中所蕴含的再现、互动和构图意义,再从情感、判断和鉴赏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图片所投射的评价意义。可以看到,在西方媒体关于巴黎恐怖袭击的相关报道中,主流的配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对恐袭遇难者的悼念(如图 1)和对恐怖袭击嫌疑犯的特写(如图 2)。而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所配发的图片也可以分为两类:对恐袭遇难者的悼念以及对恐袭后巴黎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描绘(如图 3、图 4)。
 |
| 图1 对恐袭遇难者的悼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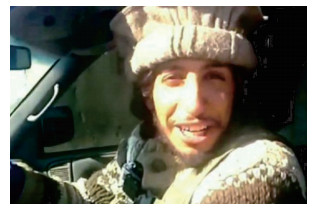 |
| 图2 恐怖袭击嫌疑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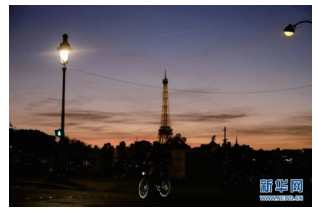 |
| 图3 恐袭后的巴黎暮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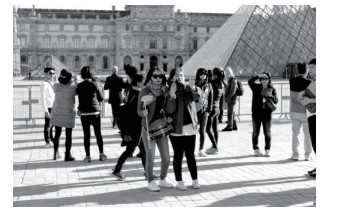 |
| 图4 恐袭后的巴黎歌剧院 |
首先,从再现意义来看,图 1展现的是一个概念过程,即找不到任何矢量来连接各个再现参与者。在该图片中,迷你的埃菲尔铁塔象征巴黎,而点燃的蜡烛表达了作者的悼念和缅怀之情,虽然主要是描述事物,但它们反映了民众悼念在巴黎恐怖袭击中丧生的无辜百姓,间接表达了创作者消极的现实型情感(非快乐)对恐袭造成的伤亡感到悲伤。另外,作者也借此间接地表达了对恐怖袭击事件的消极鉴赏,恐怖袭击非人道和残忍,应该受到谴责和控诉。该鉴赏属于社会价值层面的评判。图 2表现了一个叙事过程,即恐袭的嫌疑犯坐在车内,面露微笑。其中的矢量就是恐怖分子的视线,其眼神直视读者,因此与画面外的互动参与者形成了一种交流。表面上,该图像表露了一种积极的现实型情感快乐,但是这个叙事过程间接反映了恐怖分子的冷血和无情,从社会约束层面对恐怖分子进行了消极的判断,即:在发动了惨无人道的袭击之后还一笑置之,图片隐蔽地表达了报道者对他们的消极判断人性泯灭。
图 3和图 4都反映了叙事过程。图 3描绘了一个巴黎市民暮霭中单车骑行的场景,矢量是单车运动的方向;图 4叙述了一群中国游客在巴黎著名景点游览和拍照留念的情景,其中游客们的视线和手势构成了矢量。这两个叙事过程向人们展示了巴黎并没有因为恐怖袭击而乱了阵脚,相反人们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这在评价系统里面属于”社会评判”,即:包括巴黎民众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具有乐观向上、勇敢坚毅的品质。从鉴赏的角度来看,反映了报道者对恐袭后巴黎社会秩序迅速复原、社会生活及时恢复正常所表示的赞赏和认同,属于反应型的鉴赏。游客脸上的笑容和暮霭中骑单车的市民所烘托出的恬静氛围,让读者觉得恐怖袭击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其实也是间接表达一种积极的非现实情感,即对袭击过后的生活表示乐观和充满信心。
其次,从图像的互动意义来观察,图 1表达的情态是“提供”,而图 2是“索取”,因为图 1仅仅是描述一个事实,向受众提供信息;而在图 2中,恐怖分子的视线是对准图外的互动参与者读者,这种微笑的注视其实隐含了报道者对恐怖分子品行的消极判断(社会约束),即:暴徒是杀人不眨眼且以恐怖袭击为乐趣的。同时,图 2展示了非常近的社会距离,因为图片仅显示了嫌疑犯肩膀以上的部分,这通常表示亲近,是一种积极的现实型情感。但是,作者选取这张照片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清暴徒微笑的面部表情,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实还是为了突出一种消极判断恐怖分子的残忍和无人性,无论是依据道德规范还是法律都是不可饶恕的。从取景的视角或态度来看,图 1是一个俯视视角,突出了读者的审视权,报道者通过图片中烛光和爱心这些象征属性来间接烘托恐怖分子的残忍,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情感和态度。图 2是一个平视视角,表示融入,让受众感同身受地体会暴徒的冷酷和残忍。
在中方媒体报道中,图 3体现了“提供”的情态,向读者展示恐袭过后生活恢复平静;而图 4是一种“索取”的情态,图中的游客可以向读者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巴黎是平静和安全的,能够增强民众对法国的信心。在社会距离方面,图 3和图 4都属于远距离的构图,因为人物基本只占据画面的一半左右,故意拉开受众和再现参与者之间的距离。这显示了报道者要求受众冷静和理性地来看待恐袭,不要让恐惧妨碍自己原本的旅行和生活计划;表达了报道者对恐袭之后社会能够恢复正常的一种积极鉴赏,是对法国的支持。从取景的视角来看,图 3和图 4都采用平视视角切入,强调了平等和融入感,能让读者感受到法国宁静、安详和安全的氛围,体现出一种积极的现实型情感,再次强调危险已经过去,恐袭过后生活一切照旧,给生活在巴黎的民众和即将前往那儿的游客提供信心。
最后,从构图意义来看,图 1是一个中置布局,埃菲尔铁塔位于中心,是最关键的信息,点燃的蜡烛围绕着它,表明民众的悼念和支持;图 2是一个左右布局,左边是车内空间,是已知信息,而右边是嫌疑犯,是新信息,突出了疑犯的形象和表情。图 3是一个顶底布局,提供理想和真实信息。可以看到,图 3也出现了埃菲尔铁塔,但它处于图片的顶部,而骑乘的市民在图片的底部。这样的布局告诉大家,人们也许对恐袭还心有余悸,认为巴黎依然危险,但是真实的情况则是一切已经恢复正常。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对恐袭事件后法国环境的积极鉴赏,和对将来生活表达的积极非现实型情感非恐惧。图 4也是一个顶底布局,上方是巴黎著名的景点,下方是游客在景点附近参观留影,其表达的内涵和评价功能非常类似于图 3,就是告诉受众:危险已经过去,巴黎已经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中西方媒体运用新闻配图所表达的评价意义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对恐袭后的巴黎能够恢复正常社会和生活秩序作出积极的鉴赏,而后者主要表达消极的情感,即:对恐袭遇难者感到难过、对恐怖分子感到憎恶和恐惧;同时表达消极的判断:对恐怖分子恶劣的品行进行谴责。
2 多模态语篇的图文互动评价机制与评价意义多模态语篇分析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不同模态或符号体系之间如何协同一致来形成整体意义以传达作者的意图,表达其态度、立场和观点。
2.1 图像与文字模态间的关系类型张德禄论述了多模态语篇各种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复合模式。典型的多模态话语形式是由于一种模态或符号系统无法完整表达作者的意图而采用另外一种或几种模态来进行补充的话语形式。这种模态之间的关系称为互补关系,而其他则属于非互补关系。互补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强化关系和非强化关系[10]。强化关系指的是以一种模态为主,其他模态为辅的符际关系,即:一种模态可以基本完整地表达作者的意图,但是另外一种或几种模态可以强化这种表意功能,如在以文本为主的新闻报道中,文字是主要的交际模态,而图片则是辅助的表意系统。非强化关系表示两种或多种模态缺一不可,任何一种模态都无法单独表达完整的意义,只能共同作用来完成意义的构建,如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图像和声音就必须相互协同才能产生完整的意义。
非互补关系指的是另一种模态对意义构建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附加模态的形式出现。“这种关系一般体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交叠、内包和语境交互。” [10]交叠现象是两种模态同时出现,但它们并没有互相强化,而只是通过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一致的信息。内包是一种模态所表达的意义包括了另一种或几种模态所表达的意义总和,它们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语境交互指的是模态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独立语境和语境依赖两种。如果多模态话语和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并无直接联系,那么这种语境就是独立语境;如果话语和环境之间是相关的,那么话语的表达就会对环境产生依赖性,语境对话语的表达会产生支撑作用。
这种模态间关系理论同样适用于图文互动的复合评价模式,因为多模态语篇的评价意义也是其表达的整体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文互动的评价模式可以分成两种情况:(1)文字和图片表达的评价意义不尽相同,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支持和印证的关系,以增强新闻语篇的整体劝服能力;(2)文字和图片的评价意义相近,两者之间存在强化关系。
2.2 图文互动产生的综合评价意义通过对巴黎恐怖袭击报道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到,西方主流媒体关于巴黎恐袭的报道绝大部分配以图片,但在很多报道中,图片与报道内容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些报道中的图文关系,基本可以概括为非互补关系中的语境交互,即:图片作为文字报道的语篇环境而存在,但又不是直接相关。如题为“法国警察突袭巴黎北部后,两名恐怖分子嫌疑人死亡”(2 terror suspects dead after French police raid north of Paris)(华盛顿邮报,2015年11月18日)的报道中的插图是两个巴黎市民在街头相拥哭泣的情景,表达了报道者的消极情感对恐袭造成的伤亡表示伤心和遗憾。题为“法国开始向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让步”(France starts coming to terms with its worst-ever terrorist attack)(经济学人,2015年11月15日)的报道主要讲述法国如何应对恐怖袭击,但是配图却是一幅悼念恐袭遇难者的图片(图 1)。题为“巴黎恐袭之夜对欧洲意味着什么面对恐怖袭击欧洲是何等脆弱”(What Paris’ s night of horror means for Europe-How Europe has become more vulnerable to terrorist attacks)(经济学人,2015年11月14日)的报道主要论述欧洲各国存在哪些薄弱环节,从而给了恐怖分子可乘之机,而配发的图片是巴黎的一个著名建筑物降半旗向受袭者致哀的场景。这几篇报道主要是讨论法国和欧洲在这次恐袭之后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文字部分表达的评价意义是消极的社会评判巴黎的懦弱“让步”以及消极的价值鉴赏欧洲的“脆弱”,但配图都是表达对受害者的悼念,是一种消极的现实型情感非快乐,从而为采取各种必要安全措施提供支持和佐证。在图片提供的悲情语境下,报道的劝服力得到了增强,这比在报道中配发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的图片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在这一类报道中,图片和文字的评价意义是相互支持的,借以综合表达报道者的完整立场:巴黎不应该让步,欧洲应该强硬。
在西方媒体对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中,还有一部分多模态报道,其中文字和图片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它们通常是一种强化型的互补关系,即:报道以文字为主,图片主要是用来为整体意义提供强化和支撑。如:题为“一个新的伊斯兰国视频威胁要对华盛顿展开巴黎式的恐怖袭击”(A new Islamic State video threatens a Paris-style attack on Washington)(华盛顿邮报,2015年11月16日),这则报道的配图是ISIS公布的威胁袭击美国的视频截图,图中全副武装的ISIS成员威胁向美国发出类似巴黎的袭击。这与文字报道非常契合,图文关系属于强化型互补,文字和图片都表达了消极的非现实型情感非安全(威胁),从而强化了这种评价功能。该文还另外配发了一张巴黎恐袭嫌疑犯微笑示人的照片(图 2)。这些图片与同一时间段内媒体中大量的表达哀悼和悲伤的图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者或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受到一篇报道的影响,一段时期持续的新闻报道才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这些多模态新闻报道其实可以传递一种整体的评价意义:恐怖分子的凶残和没有人性(如图 2),受袭击民众是无辜和脆弱的(如图 1),前者通过与后者的对比凸显出来,从而可以劝服和引导人们厌恶和鄙视恐怖分子,为西方即将对恐怖分子展开的严厉打击获得民意支持。
相比之下,在中国主流媒体对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中,图片和文字一般都紧密相关,形成一种强化型的互补关系,即:报道以文字报道为主,新闻配图为辅,文字和图片的评价意义基本相同。同时,中国主流媒体对巴黎恐袭报道的评价侧重点也与西方媒体有所不同。一方面,中国媒体的报道也对恐怖袭击表示谴责(消极的鉴赏),对遇难者表示哀悼(消极的现实型情感),如题为“巴黎发生多起枪击爆炸袭击上百人死亡”(环球时报,2015年11月14日)的报道中的配图就是急救人员用担架抬着伤员送往救治点的情景。该报道的文字和图片表达的评价意义基本一致,主要是对恐怖袭击这种残忍和非人道的行为进行消极的价值鉴赏,图片中被送往医院急救的伤员可以用最直观的形式来强化这种评价,潜在地影响受众的认知。另一方面,中国媒体把报道和评价重心放到了恐袭过后社会生活秩序的恢复上。例如,2015年11月16日,《环球时报》一篇以“中国游客仍在巴黎拍照购物:巴黎不像想象中可怕”为题的报道描述了在巴黎全城戒严的情况下,国人一大早就去歌剧院照相(文中所称的歌剧院并非遭袭的巴塔克兰剧院,而是巴黎歌剧院),随后还去拉法耶特商场购物的情景。该报道的配图则是中国游客依然在巴黎街头拍照留念(图 4),图文相互配合,从社会价值层面作出的积极鉴赏,对巴黎人民的乐观和坚韧表达了积极的社会评判,从而文字和图片所表达的评价意义相互呼应,强化了多模态新闻语篇的劝服效果,表达了对巴黎恢复正常秩序和维护安全保障的信心,是对受到恐怖袭击的法国人民的支持。
实际上,中方媒体在对整个事件的报道,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运用这种强化型互补的关系。例如,另一篇题为“巴黎恐袭可能由三组恐怖分子协调完成”(新华网,2015年11月15日)的报道中,配图是在法国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将写有“我们不害怕”字样的纸牌与蜡烛放在一起,悼念恐怖袭击遇难者。报道援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评价对“卑劣而野蛮”的袭击行径“深表震惊”,并认为此次恐怖袭击不仅针对法国民众和巴黎,而是对“整个人类和奥林匹克价值的攻击”。文字报道部分对恐怖分子的品行作出了消极的判断(社会约束),而图片部分则对法国人民的品质作出了积极的判断坚强乐观(社会评判),文字部分的评价更加强化了图片的评价效果恐怖分子再凶残也不能让法国人民屈服。新华网11月15日的另一则报道题为“巴黎恐怖袭击之后的街头”,新闻配图是一名男子骑车从法国巴黎市区经过(图 3),这也构成一种强化型的互补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对于巴黎恐怖袭击的报道充满了正能量,它们对法国人民表示了积极的社会评判勇敢、坚毅、不折不挠,对法国社会的鉴赏也是积极的。中国媒体没有直接对恐袭进行批评和指责,而是通过对恐袭过后巴黎能够迅速恢复社会生活秩序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媒体在报道时,特别是运用图片模态进行评价时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会对受众的意识形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总之,在对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中,中西方媒体的评价倾向是有较大差别的,即中国媒体的报道表明法国和欧洲仍旧是安全的,表示信心和提供支持;而西方媒体的报道更多的是反映对逝者的哀悼,表达悲伤的情感,间接地对恐怖分子作出消极评价,发出严厉的控诉。这其实是和中西方媒体不同的报道理念紧密相关的。西方传媒的报道取向一般遵从“以事为本”的原则,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细致深入,不回避任何悲情、负面的元素,而且往往刻意展露灾难细节。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倾向于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进行灾难事件报道时,往往侧重表达人是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突出乐观积极的情绪,肯定人的精神力量[16]。
3 结语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媒体运用多模态新闻语篇对巴黎恐怖袭击所进行的报道,可以发现:视觉语法可以有效地揭示新闻图片的意义和内涵,但其评价意义并不是外显的,需要运用评价理论进一步发掘出其中潜藏的情感、态度和观点,新闻报道配发不同的图片往往可以达到不同的评价效果。作为一种隐蔽而有效的评价资源,新闻图片可以增强报道的劝服效果,潜移默化地引导社会认知和舆论走向。在多模态新闻语篇中,一般以文字报道为主、新闻图片为辅构成一个整体的评价意义,可以运用模态间关系理论来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整体评价意义的形成模式。
| [1] | Martin J R, P R R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
| [2] | 王振华"硬新闻"的态度研究.[J].外语教学, 2004(5): 31-36. |
| [3] | 刘世铸, 韩金龙. 新闻话语的评价系统[J]. 外语电化教学, 2004 (4) : 17 –21. |
| [4] | Bednarek M. Evaluation in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rpus[M].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 |
| [5] | 王天华. 新闻语篇隐性评价意义的语篇发生研究[J]. 外语学刊, 2012 (1) : 104 –107. |
| [6] | 刘世铸. 评价理论在中国的发展[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 (5) : 33 –37. |
| [7] | Kress G, Van Leuwen T.Reading images: The grammer of viusal design[M].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006. |
| [8] | Martinec R, Salway A. A system for image-text relations in new(and old)media[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5, 4 (3) : 337 –7l. DOI:10.1177/1470357205055928 |
| [9] |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 外语学刊, 2007 (5) : 82 –86. |
| [10] | 张徳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 中国外语, 2009 (1) : 24 –30. |
| [11] | 李战子, 陆丹云. 多模态符号学:理论基础, 研究途径与发展前景[J]. 外语研究, 2012 (2) : 1 –8. |
| [12] | Martin J R, D Rose. Working with Discourse-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M]. London: Continuum, 2007 . |
| [13] | 陈瑜敏. 奥运电视公益广告多模态评价意义的构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 108 –114. |
| [14] | 冯德正, 亓玉杰. 态度意义的多模态建构基于认知评价理论的分析模式[J]. 现代外语, 2014 (5) : 585 –596. |
| [15] | 石春煦, 王振华. 多模态历史教科书中评价语义的图文双重建构[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 (9) : 8 –14. |
| [16] | 黄昆仑. 从" 9 · 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的差异[J]. 现代传播, 2001 (1) : 56 –58. |
 2016, Vol. 18
2016, Vol.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