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它强调中国传统哲学、吐纳养生健身与武术技击相结合,通过儒家的“自修”和道教的“内修”最终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修养状态。太极拳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符号和识别码,因深厚的文化底蕴、柔和的运动形态及独特的健身效果备受国内外练习者追捧。资料[1]显示,太极拳已传播至世界范围内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习练人数近1.5亿人。
针对太极拳的跨文化传播,我国众多学者从其传播的意义[2-4]、理论[5-7]、途径与策略[8-9]、传播过程中的译介[10-12]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截至2019年12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建成36个中国文化中心[13],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在全球162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545所孔子学院和1 170个孔子课堂[14]。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太极拳在海外的传播,特别是如何通过孔子学院的平台进行国际传播,并展开相关课题研究[15-18];但多数研究仅停留在对太极拳在某国或地区开展现状的研究,缺乏对太极拳在该国或地区的传播历程、跨文化传播动力以及传播现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深度研究。
对此,笔者对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历程与传播动力进行深层次研究,旨在考察“全球化”视域下太极拳在海外的传播与变迁,并希冀能够为太极拳的“全球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以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历程为切入点,以英国的部分太极拳传播者、受众、太极拳组织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采用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英国太极拳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点”“面”结合,通过描述不同阶段的特征,勾勒太极拳在英国传播的全貌。
2.2.2 文本分析法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在了解英国太极拳传播的关键节点、人物、组织的基础上,对英国的太极拳传播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并对太极拳在英国传播过程中的动力学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探寻太极拳跨文传播的规律以及太极拳在英国变迁的原因。
2.2.3 访谈法在文献资料与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就太极拳在英国传播的作用与影响,英国太极拳传播过程的关键人物、事件以及太极拳组织等进行访谈。实地走访英国太极拳协会组织以及英国各地区有影响力的太极拳俱乐部(一般有数十年的营业历史),例如伦敦的道教功夫俱乐部、布里斯托的陈式太极拳俱乐部、蒙茅斯郡的养生太极拳俱乐部、利物浦的陈式太极拳俱乐部、伦敦的吴式太极拳学院、曼彻斯特的太极拳俱乐部、伯明翰的螳螂功夫俱乐部、卡迪夫的太极拳俱乐部、爱丁堡的武当太极拳俱乐部和格拉斯哥的洪拳俱乐部等,并对相关专家学者、太极拳俱乐部资深教练员以及部分太极拳习练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由此获取太极拳在英国传播与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3 太极拳在英国传播的历程与阶段特征以太极拳传播过程的主要特征为主线,以在英国搜集的太极拳传播的文献与访谈资料为支撑,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将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道教文化”启蒙阶段、“杨式太极”主导阶段、“多家流派”发展阶段。
3.1 “道教文化”启蒙阶段(—1949年) 3.1.1 启蒙阶段的背景阐释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面对清政府的无能,许多有志之士不得不求助于其他方式救亡图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许多武术家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捻军起义(1852—1868年)、义和团运动(1898—1900年)等,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武术的发展。为了保卫和重振当时支离破碎的中国,无论是1910年成立的精武体育会,还是1928年创办的中央国术馆,其宗旨都是通过倡导国人习练“国术”而强身健体,为中华崛起而贡献力量。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公开教授武术,不仅对消除门派之争、门户之见发挥了强大的助力作用,对中国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加速了太极拳以家族姓氏为标志的流派或风格的形成,为日后太极拳的“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尽管近代中国面临着诸多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也遭遇“文化紧张”“文化焦虑”,但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还是受到了西方哲学家的关注。例如,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和马赛尔·莫斯等都对道教哲学非常感兴趣,这也为太极拳在英国乃至西方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哲学基础[19]。
3.1.2 启蒙阶段的传播者苏奇[20](Chee Soo,1919—1994年)出生于伦敦的马里波恩(Marylebone),是一名中英混血儿。他的父亲苏安奇(Ah Chee Soo)是中国人(威斯敏斯特餐厅的糕点师),母亲Beatrice Soo是英国人。据苏奇回忆:1926年他被一名英国慈善家Thomas John Barnardo创办的孤儿院收养;14岁时在海德公园结识李陈金(Chan Kam Lee),并被其收养为侄子;1934年夏天,在李陈金的严格指导下开始对“李式武术”进行系统的学习与训练;1936年10月应征入伍;退伍后,于1948年在伦敦West Ham创办Manor Road School,开始教授以道教文化为基础的“李式武术”。20世纪60年代,由于所教授的“李式武术”在伦敦颇具影响力,苏奇被当时热映的电视剧《复仇者》(The Avengers)导演雷·奥斯汀(Ray Austin)聘为武术指导,出现在《复仇者》的宣传海报(图 1)上。苏奇在其传授“李式武术”的一生中,不仅教授武术,还出版了《中国太极拳》(The Chinese Art of T'ai Chi Chuan)、《凯门道教术》(The Taoist Art of K'ai Men)等多本有关道教文化、中国武术、道教养生的书籍。他不仅为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道教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 图 1 雷·奥斯汀和苏奇的宣传照 Figure 1 Movie poster of Ray Austin and Chee Soo |
该阶段的传播内容确切地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养生气功和中医的综合体,是对太极拳同源文化的传播。尽管很多人认为苏奇教授的“李式太极拳”不是太极拳,但可以肯定的是,太极拳相关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便存在于英国。这种现象表明,中国传统养生术、气功以及具有养生和技击双重功能的太极拳在英国具有吸引力,且拥有一定的“潜在”受众。
3.2 “杨式太极”主导阶段(1950—1980年) 3.2.1 主导阶段的背景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极拳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成为服务大众健康、娱乐的一种手段。为更好地服务大众,传统太极拳被简化、标准化。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于1956年组织太极拳专家,汲取杨式太极拳之精华创编“24式太极拳”。在“文革”期间,许多太极拳习练者和武术家受到冲击,不少太极拳师迫于无奈而移居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或一些亚洲国家;太极拳被彻底改造,一些文化元素丧失。同时,那些通常只向“拜师徒弟”传授的技术,如某些特殊练习方式、太极拳格斗技巧等,在传承过程中也逐渐丢失。太极拳开始成为一项健身养生的体育项目,而其技击对抗功能被逐渐弱化[21]。
3.2.2 主导阶段的开拓者Gerda Geddes(1917—2006年)是英国太极拳传播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22]。她原是挪威著名舞蹈家、心理学家,1948年随丈夫来到上海,第1次接触并迷上太极拳;1955年,在香港拜蔡鹤朋为师,学习传统杨澄甫式拳架3年,学成后移居英国并开始在英国传播太极拳;1959年,通过电视台让英国人认识了太极拳;1960年,在伦敦现代舞蹈学院开班授课。此后近40年间,Gerda Geddes通过课程、书籍、影像以及网络等方式持续宣传太极拳,也由此改变了数万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她认为太极拳不仅是一套强身健体的拳法,也是一种艺术存在的形式,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
| 图 2 Gerda Geddes练拳、教拳照 Figure 2 The pictures of practicing and teaching Taiji Quan by Gerda Geddes |
Paul Crompton(1936—)是英国太极拳理论传播的杰出贡献者,也是国际公认太极拳领域的权威作家[23]。他的许多经典著作(图 3)是西方太极拳习练者的必备资料,主要包括Tai Chi Workbook(1987年)、Tai Chi for Two:The Practice of Push Hands(1989年)、Tai Chi Combat(1991年)、The Art of Tai Chi(1993年)、The Elements of Tai Chi(1994年)、Tai Chi: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Discipline(1996年)、Tai Chi:A Practical Introduction(1998年)、Tai Chi: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Chinese Art of Movement(2000年)、Tai Chi for Beginners(2003年)。他从1972年开始教授传统杨式太极拳,至今已有40多年,并通过对太极拳文献的整理,为其理论传播乃至中国武术在英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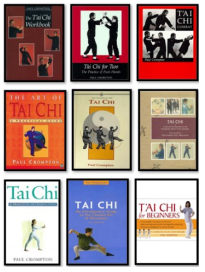
|
| 图 3 Paul Crompton的太极拳著作 Figure 3 Paul Crompton's Taiji Quan books |
John Kells(1940—2017年)是英国具有开拓精神的太极拳传播者[24],1967年开始学习太极拳,先后向梁通才(Liang Tung-Tsai)、朱振舜(Chu Gin-Soon)和杨守中(Yang Shou-Chung)学习杨式太极拳。1970年,他在伦敦创建英国太极拳协会;1977年,开始全职教授太极拳;1977—1993年,教授的学生达万余人。1991年,他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养生锻炼方式,把杨式太极拳与欧洲一种古老的自我修炼方法相融合,创建被称为“心灵工作”(heart work)的健身养生法。他鼓励学生将习练太极拳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告诫他们要通过习练太极拳提高自身健康水平,通过身体运动关注自我。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移民在太极拳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太极拳原来的只在华人社区自我传播开始走向真正的西方社会。李绍强与朱景雄就是其中的典型。
李绍强(Rose Li,1914—2001年)出生于北京的富裕家庭,父亲是清政府官员,负责中国的煤炭工业[25]。由于2个姐姐幼年夭折,其父为其起名“绍强”,希望她能健康成长。李绍强8岁开始师从邓云峰(1873—1941年)、刘凤山(1852—1937年)习练八卦掌、形意拳、吴式太极拳;1947年,在美国圣公会(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帮助下移民美国;195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心理学。在美期间,她先在旧金山、纽约和夏威夷等地教授中国内家拳(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后在密歇根的安阿伯大学教授中文并传播中国文化。1975年移居英国,在杜伦大学东方研究系工作的同时,还在杜伦、曼彻斯特和伦敦等地教授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随着伦敦学员人数的增多,1986年她定居伦敦,直至2001年逝世。
朱景雄(Chu King-Hong,1945—)是杨澄甫长子杨振铭(字守中)的入室弟子,出生在广东省,后移居中国香港[26]。1957年,朱景雄开始跟杨守中学习传统杨式太极拳,后经师父允许,开始教授传统杨式太极拳。1974年,他创办国际太极拳协会(International Tai Chi Chuan Association,ITCCA),开始在英国传播传统杨式太极拳。他主要教授传统杨式太极拳、传统杨式太极剑、形意拳和长棍。随着ITCCA的不断发展,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均已开设分会,朱景雄的很多学生也成为传统杨式太极拳在英国乃至欧洲传播的中坚力量。
3.2.3 主导阶段的特征(1)传播内容与形式单一化。在本阶段,主要传授的太极拳流派以杨式太极拳为主。如:Gerda Geddes主要教授杨澄甫式太极拳;Paul Crompton主要教授郑曼青根据传统杨式108式改编的37式太极拳,也被称为“郑子简化37式太极拳”;朱景雄主要教授杨守中传授的传统杨式太极拳。
本阶段的传播形式多以“太极拳课程”为主。虽然“课程传播”的形式比较单一,但是这种核心的传播形式有其特殊性,它是由太极拳传播者运用课程把太极拳的文本意义以听觉、视觉、感觉、触觉等“通感”的媒介方式与太极拳受众互动,传播质量较高。
(2)传播目的养生化。去技击化,倡导养生化、修身化和艺术化是本阶段传播的一大特征。Gerda Geddes教授学生在练习太极拳套路时采用4种不同的呼吸方式,通过对呼吸的关注体认自我的存在,认为通过这样的练习就会气血畅通、全身通达,久而久之便能达到延年益寿之功效[22]。Paul Crompton教授学生习练太极拳时要求不要有负面情绪,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感知身体、放松身体上,用太极拳认知自我、认知自然,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23]。李绍强注重对太极拳艺术和哲学层面的理解,教导学生把太极拳作为理解、体验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她时常告诉学生:“我以儒家观念理解个人关系,以道家思想理解神与自然的关系,对你们而言,跟我习练太极拳不仅是学习身体动作,而是通过习练太极拳深入接触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25]
3.3 “多家流派”发展阶段(1981年—) 3.3.1 发展阶段的背景阐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将工作重点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27]。在文化领域也同时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确立了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太极拳在此背景下有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国家体委及武术研究院组织专家集体精心编排了48式太极拳;1988年,原国家体委组织专家共同创编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太极拳竞赛套路——42式太极拳,后者在1990年的第11届亚运会上得到推广。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基本成型,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系列“文化走出去”政策为本阶段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3.3.2 发展阶段的主要传播者Dan Docherty(1954—)现任英国太极拳联合会(Tai Chi Union for Great Britain)主席,是欧洲最著名的太极拳推广者之一[28]。他于1954年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1974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并获法学学士学位;1975年移居中国香港并担任皇家香港警察局督察,且抵港不久便拜师郑天雄学习武当太极拳。与大多数英国太极拳推广者不同的是,Dan Docherty具有实战经历,在向郑天雄学习武当太极拳的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中国香港综合格斗比赛的冠军,1980年在马来西亚参加第5届东南亚武术锦标赛还获得无差别级格斗冠军。1984年,他返回英国,在伦敦创办“实用太极拳学校”(Practical Tai Chi Chuan School),教授内容为武当太极拳套路、器械、散手和内功。1987年,在伦敦组织了第1届英国太极拳推手比赛,采用中国古老的擂台形式进行比赛。这次比赛对将太极拳视为冥想艺术并将比赛视为世俗体育文化的太极拳推广者而言是一次严重“打击”,促进了太极拳向“实用、实战”的风格转变,使杨式、吴式、陈式、孙式和武式太极拳等流派开始重新关注太极拳的技击功能,同时也使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Gary Wragg(1946—)是英国著名画家,英国最主要的太极拳传播者之一,吴式太极拳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英国太极拳联合会创始人、前任主席、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技术小组成员[24]。他从1973年开始先后跟随Gerda Geddes、John Kells学习杨式太极拳。1979年,在伯爵宫(Earl’s Court)学习吴式太极拳;1983年,在伦敦创建吴式太极拳中心(The London Centre of Wu Style Tai Chi Chuan),开始教授吴式太极拳。1983年,赴加拿大拜师吴光宇(Wu Kwong-Yu)学习吴式传统太极拳;1989年,将吴式太极拳伦敦中心更名为“吴式太极拳学院(Wu’s Tai Chi Chuan Academy)”,这是欧洲第一所吴式太极拳学院。Gary Wragg对吴式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Danny Connor(1944—2000年)是英国太极拳传播史上首位教授“24式太极拳”“48式太极拳”等国家标准太极拳套路的传播者[29]。20世纪60年代,他在日本与太极拳结缘,并在新加坡学习了郑曼青的“37式杨式传统太极拳”。1972年,他在曼彻斯特创办“东方世界”太极拳馆并开始教授太极拳。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学习“24式太极拳”“48式太极拳”和太极器械等国家竞赛规定套路,学成归国后继续教授太极拳,直至逝世。由于Danny Connor的积极推广,越来越多的英国受众了解、习练并参加太极拳竞赛,促进了英国太极拳的发展,并对太极拳国家竞赛规定套路的推广起到助力作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的实践者们一直在探索太极拳与其他艺术、治疗以及冥想练习之间的潜在协同作用。Linda Chase Broda(1941—2011年)就是这样的践行者[30]。1974年,她在爱丁堡开始学习杨式太极拳,后来又师从Ian Cameron学习武当太极拳。1980年,她在曼彻斯特创建“Village Hall Tai Chi”太极拳学校,并开始向温顿医院(Withington Hospital)神经科、精神病科的病人教授太极拳。在其授拳生涯中,她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太极拳的干预使病人能够康复,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随着“补充和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的提出与科学研究对太极拳和气功健身效果的验证,养生气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与重视,越来越多的英国习练者开始探索太极拳、气功的潜在治疗效果。很多太极拳培训机构、学校以及组织的课程越来越倾向养生健身的内容。Michael Tse和Jason Chan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Michael Tse原来是一名中国香港警察,在Danny Connor的支持与帮助下,于1991年在曼彻斯特创建“谢气功中心”(Tse Qigong Center),并创办《气杂志》(Qi Magazine)。他主要教授道教“大雁”气功、陈式太极拳和咏春拳,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气功教师之一。Jason Chan在中国香港学习咏春拳,抵达英国后教授咏春拳、太极拳,随后以太极拳、气功与道教导引术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新的健身养生方式,并命名为“无限太极”(Infinite Tai Chi)。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批具有武术技能的海外新移民为中国武术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李晖(Faye Li Yip,1968—),太极拳优秀传播者李德印之女,自幼随父习武,酷爱武术[31]。1990年,在伯明翰城市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求学期间一直推广、宣传中国太极拳、气功与养生文化。毕业后她专注于太极养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推广:1996年,与丈夫叶立威在英格兰的特尔福德(Telford)建立德印太极拳学院(Deyin Taiji Quan Institute);2009年,在中国健身气功中心的支持下成立英国健身气功协会。李晖目前担任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执委会委员,英国太极拳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国际武当文化英国分会会长,主要教授杨式、孙式太极拳和国家规定套路。
岳黎明(1964—)是从中国大陆赴英国传播陈式太极拳的开拓者之一,早年习练少林功夫,后在陈家沟跟随陈正雷习练传统陈式太极拳,1998年被陈正雷收为入室弟子,之后又随南岳山道士习练内功[32]。1995年他移居英国,于1997年在曼彻斯特建立“陈式太极拳中心”,该中心随后迅速成为陈式太极拳在英国传播的重要阵地。陈式太极拳是21世纪在英国发展最快的一支流派。岳黎明对促进陈式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3.3.3 发展阶段的特征该阶段在传播内容、形式、渠道、组织、目标等方面均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
(1)传播内容。传播内容的多样化主要体现为:①流派多样化,如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李式太极拳、武当太极拳等多种流派共存;②套路多样化,例如,杨式太极拳主要有郑子简化37式太极拳(郑曼青)、杨式传统太极拳(杨守中)、董式太极拳(董英杰)等,陈式太极拳主要有老架、小架、新架等;③习练形式多样化,如套路、器械、推手、散手、太极养生、实战等。
(2)传播形式。在英国,以往最常见的太极拳传播形式是太极拳课程,而该阶段开始出现各类太极拳比赛、专家研讨会、研习班以及实地探访的寻根问祖班等多种形式,不但丰富了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形式,为太极拳课程形式提供有益补充,也促进了国内知名太极拳传播者的对外交流,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交流机制,为更多英国太极拳培训机构、太极拳俱乐部、太极拳流派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机会。
(3)传播渠道。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本阶段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渠道呈现了多样化现象。从“书籍报刊”传播到“广播影视”传播,再到“网络互动”传播,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不仅多样化而且形成了“课程培训”“组织比赛”“科学研讨”等多种渠道立体传播的局面。多样化传播渠道使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受众”与“受众”的距离都大大缩短。
(4)传播组织。在本阶段,组织对太极拳在英国的有序传播起到很大的助力作用。1991年,英国太极拳联合会创立,它独立于英国的中国武术传播组织,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包容性的太极拳传播组织,是英国不同太极拳流派、风格的代表机构。2000年,由Linda Chase Broda发起建立了“太极和气功健康论坛”(Tai Chi and Chi Kung Forum for Health)[30]。该组织主要通过科学研究(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力学等研究)证实太极拳的健康功效,不仅提高了太极拳在英国社会的认知度,而且也为英国太极拳从业者的正当性提供了科学依据。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流派成立各自的太极拳组织,太极拳组织的多样性也是该阶段的一大特点。
(5)传播目标。1987年,Dan Docherty在伦敦组织的首届太极拳推手比赛向英国太极拳界宣告了太极拳技击的重要性,并且通过这次比赛促使各流派开始注重太极拳的技击功能。此次太极拳推手比赛是英国太极拳传播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从此之后,各太极拳流派不但重视养生效果、艺术追求,而且也开始向太极拳的“实用、实战”风格转变,逐渐形成“养生技击”并重的传播局面,即英国太极拳受众习练太极拳具有不同目标:有的人是为了健康养生,陶冶情操;有的人是为了实战,提高格斗技能,体验东方以退为进的技击术;也有的人是为了提高身体的艺术修养等。受众需求的多样性使得太极拳传播的目标更加多样化。
4 太极拳在英国传播过程的变迁 4.1 太极拳传播内容的变迁目前,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内容可以分为套路、器械、推手、散手等4种形式。
在套路上,由原来招式繁多向精简转变。例如,在英国非常流行并占有重要地位的“郑子简化37式”,便是由郑曼青根据杨澄甫所传授的传统杨式108式(国内也很少人习练)改编而来。在套路的使用上,在英国有着良好传播基础的实用太极拳是Dan Docherty从中国香港郑天雄处习得的武当太极拳。此类太极拳在国内也很少有人知晓,并且与国内的武当太极拳不是同一概念。
在套路的内容创新上,一些传播者根据需要创造了新的套路:有的套路是为提高教学效率,减少一些传统套路的重复招式动作;有的套路是针对特定群体,如Linda Chase Broda针对老年神经科和精神病科病人进行创编的太极拳套路。
在推手方面,虽然双人对练相对普遍,但对技击技术的重视程度逐渐变弱。相对套路和推手而言,器械训练、格斗应用的课程受关注度越来越低。
4.2 太极拳认知的变迁在国内,多数人认为太极拳是武术。在英国,对太极拳的公众认知更侧重于其冥想与健身养生功能。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过度宣传太极拳的健身养生功能使得英国公众对太极拳形成刻板印象——太极拳是中国的一种延年益寿的养生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太极拳健身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一些太极拳干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使得英国公众对太极拳的认知更加倾向于其治疗功效,同时也更加削弱了对太极拳技击功能的认知。在英国,关注太极拳技击功能、参与太极拳实战并期望提升实战力的受众占极少数,而期望通过太极拳习练提高自身健康水平的受众占绝大多数。并且,对不同太极拳谱系风格的认知也出现变迁并在英国受众中形成固定模式。例如,杨澄甫传承的杨式太极拳通常被认为具有以健康为导向的风格,而武当太极拳则通常被认为具有以武术技击为导向的风格。
4.3 太极拳组织的变迁太极拳组织对于太极拳的传播和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太极拳组织在英国也发生变迁,由最初流派组织的交流与互助向全国统一组织的自治转变。太极拳组织的全国统一自我管理是在英国体育协会认可下的高度自治,为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提供了保障。英国太极拳联合会的自治使得太极拳在英国的发展变得“有序”。英国太极拳联合会是目前英国最权威的太极拳教练员认证机构,具备英国太极拳的唯一认证系统。英国太极拳联合会将太极拳教练员分为4个等级:①资深教练员(Senior Instructors,SI),通常至少有20年的中国内家拳习练经验;②高级教练员(Advanced Instructors,AI),通常至少有8~10年的中国内家拳习练经验;③中级教练员(Intermediate Instructors,II),中国内家拳习练到可接受的水平;④初级教练员(Basic Instructors,BI),自身继续习练中国内家拳,能够胜任初级水平的教学,并会定期接受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水平[33]。太极拳教练员注册名单从1993年的55人增加到目前的656人(表 1)。2000年,Linda Chase Broda建立的“太极和气功健康论坛”为太极拳的健康养生功效提供了科学支撑。英国太极拳联合会和“太极和气功健康论坛”的出现凸显了太极拳在英国“养生”与“技击”并重的发展特征,这种联合模式的自治组织对太极拳的“武术技击”和“养生康复”双重属性的传播起到助力作用。
| 表 1 英国注册太极拳教练员地区分布一览 Table 1 Information list of registered Taiji Quan instructors in UK |
无论是在“道家文化”启蒙阶段,还是在“杨式太极”主导阶段,抑或在“多家流派”发展阶段,健身养生是太极拳在英国传播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反映在练习人口数据上:在英国习练太极拳的人群中,女性占有很高的比例,并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参与者为主[34]。这种年龄和性别特征表明了一个公众意识:虽然太极拳是融技击、健身、养生、冥想与休闲于一体的武术拳种,但是英国受众更注重的是其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养生思想。特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太极拳在“补充和替代医学”中的有效性[35-38]。尤其是太极拳健康干预研究成果被世界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39-40]后,更加证实太极拳在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太极拳的“健身养生”功效被大规模推广与宣传,这也是其在英国传播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
5.2 “技击对抗”是传播与发展的竞技动力因素太极拳“技击”功能是在英国传播与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因素。在英国,有着良好传播基础的武当太极拳,其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太极拳的“技击”功能。由于武当太极拳“技击”功能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多英国年轻受众的喜爱,加之现任英国太极拳联合会主席Dan Docherty对太极拳的“技击”功能进行积极推广与传播,英国其他流派也开始越来越追求太极拳的“技击”实用功能。
5.3 中国香港的枢纽作用是传播与发展的交流动力因素若仅从太极拳的国际化进程考量,中国香港的特殊地位和独有文化无形中为太极拳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传播打下一定基础。无论是“道教文化”启蒙阶段的李陈金,还是“杨式太极”主导阶段的Gerda Geddes、朱景雄,抑或“多家流派”发展阶段的Dan Docherty、Jason Chan和Michael Tse,都是经由中国香港拜师学艺后去英国传播太极拳的。可见,中国香港起到了独特桥梁作用,促成了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
5.4 “功夫热潮”是传播与发展的宣传动力因素20世纪70年代,功夫巨星李小龙主导、主演的电影为“港产”功夫片带来新的变革与发展。功夫电影被成功打造成全球电影类型的一部分,并借此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亚洲人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引起了全世界受众对“功夫”的热爱,掀起了“功夫热潮”[41]。这一强烈、迅猛的“功夫热潮”也席卷了英国。笔者在访谈时得知,很多英国年长的太极拳教练员、教师起初都是因为李小龙的“功夫电影”而对中国武术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当时想习练中国功夫却找不到中国功夫武馆,无奈之下才选择了“日本武术”或“韩国武术”。当时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水平、国际化水平都高于中国,其“武术”走出国门的时间远远早于中国。可见,李小龙掀起的“功夫热潮”其实助推了“东方武术”在世界的传播。这也许是日本、韩国“武术”在国际上受众较多且成为奥运项目的主要原因。总之,20世纪70年代的“功夫热潮”对太极拳在英国的传播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
5.5 “华人移民”是传播与发展的传播动力因素海外华人移民是武术国际化传播进程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42]。他们对武术的国际化传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助力作用,是重要的动力因素之一。他们不仅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很深的理解,而且对所在国人们对武术的需求也非常了解,在传播武术的过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样,英国的华人移民是太极拳在英国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传播动力因素。例如,李晖及其丈夫叶立威建立的德印太极拳学院不仅传播太极拳,而且每年组织“中国太极、气功文化之旅”系列活动。岳黎明利用自身的资源(陈家沟第11代陈氏传人陈正雷的入室弟子,同时也是湖北武当山南岳山道士的弟子),每年举办“太极文化中国行”系列活动。这些文化活动不仅对太极拳的传播起到助力作用,而且对中英文化的民间交流起到促进作用,既减少了文化传播的“文化折扣”现象,又能增加英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直观印象。
5.6 “改革开放”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传播与发展的政治动力因素政治环境在太极拳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推崇武术为国术并成立中央国术馆,对太极拳的多流派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任国家领导人对太极拳的肯定与支持,加速了太极拳的标准化、简明化进程;1956年国家体委组织太极拳专家编排的“24式太极拳”至今仍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文革”期间,太极拳被彻底“改造”,其特定技术名称中的文化内涵被严重破坏;改革开放给太极拳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其进入快速推广普及期。目前,“48式太极拳”“42式太极拳”以及各流派的竞赛套路竞相发展。可见,政治环境对太极拳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2006年发布的《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确定了我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基本思路和框架,标志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基本成型。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43]。“文化走出去”政策为太极拳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也是太极拳在英国传播与发展的政治动力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动力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6 结束语太极拳从诞生至今,经历了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从家族传承到异族传播,从乡间村落到都市京城,从中国“普及化”到世界“全球化”,太极拳一直在变化中发展。在英国的传播过程亦是如此,太极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从“道教文化”启蒙到“杨式太极”主导,再到“多家流派”发展,在此过程中,太极拳既在传播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变迁。事物的发展与变迁离不开驱动力。太极拳“健身养生”和“技击对抗”的内动力是其在英国传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中国香港的交流枢纽作用为太极拳在英国传播提供便利条件;李小龙掀起的“功夫热潮”为太极拳在英国传播起到文化助力作用;海外华人移民是太极拳在英国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太极拳国际化发展的动力双擎,不仅促进太极拳在英国传播与发展,更为太极拳的“全球化”发展与传播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马秀杰:设计论文框架,搜集调研文献,参与英国境内的调研工作,撰写、修改论文;
高瞻:翻译英文调研文献,参与英国境内的调研工作;
Paul Bowman:提出论文选题,提供撰写、调研思路与英文文献,联系主要调研对象;
姜传银:审核、指导修改论文。
| [1] |
王柏利. 太极拳:一种标识性文化符号[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1(1): 70-74 (  0) 0)
|
| [2] |
孙喜莲, 余晓惠, 梅林琦, 等. 太极拳的国际传播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8, 42(6): 72-75 (  0) 0)
|
| [3] |
杨祥全, 杨祥国. 太极拳国际化发展的传播学思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4, 19(2): 62-65 (  0) 0)
|
| [4] |
姜南, 梁勤超, 李源.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太极拳文化符号的运用[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6, 50(1): 54-58 (  0) 0)
|
| [5] |
常朝阳. 太极拳文化海外传播的理论研究与问题消解[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5(3): 338-344 (  0) 0)
|
| [6] |
史友宽. 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考察与理念创新[J].
体育科学, 2013, 33(5): 13-24 (  0) 0)
|
| [7] |
李吉远, 郭志禹. 太极拳传播现象的文化解读[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27(2): 186-189 (  0) 0)
|
| [8] |
宋清华, 申国卿. "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战略背景下太极拳国际化传播策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8, 52(3): 61-66 (  0) 0)
|
| [9] |
任锋. 目的论对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3(1): 137-140 (  0) 0)
|
| [10] |
朱宝锋. 太极拳英语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7): 188-191 (  0) 0)
|
| [11] |
杨素香. 太极拳在美国的传播:一项基于美国大众媒体语料库的研究[J].
体育科学, 2017, 37(3): 68-78 (  0) 0)
|
| [12] |
李涛, 马秀杰. 太极拳西行传播的翻译演进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J].
江西社会科学, 2017, 37(4): 242-249 (  0) 0)
|
| [13] |
马逸珂.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布局全球, 传播中华文化[N].中国文化报, 2018-01-31(1)
(  0) 0)
|
| [14] |
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关于孔子学院/课堂[EB/OL].[2019-12-31].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  0) 0)
|
| [15] |
周玉芳. 孔子学院传播武术太极路径探索[J].
体育文化导刊, 2015(1): 199-202 (  0) 0)
|
| [16] |
韩晓明, 胡晓飞. 太极拳国际化推广问题及对策:以冰岛、挪威和喀麦隆三国孔子学院为例[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6): 20-24 (  0) 0)
|
| [17] |
郭旭霞, 王艳琼, 郭伟杰. 泰国孔子学院的体育传播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6): 130-133 (  0) 0)
|
| [18] |
郭玉江, 冯慧. 孔子学院建立太极拳培训基地的可行性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4(4): 199-202 (  0) 0)
|
| [19] |
CLARKE J J.
The Tao of the West:Western transformations of Taoist thought[M]. London: Routledge, 2000: 104.
(  0) 0)
|
| [20] |
SOO C.
The Tao of my thoughts[M]. London: Seahorse, 2006: 5-25.
(  0) 0)
|
| [21] |
RYAN A. Globalisation and the "Internal Alchemy"in Chinese martial arts:The transmission of Taijiquan to Britain[J].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2(4): 525-543 (  0) 0)
|
| [22] |
ROBINSON R.Tai Chi interview: Gerda Geddes[EB/OL].[2018-08-25].https://taiji-forum.com/tai-chi-taiji/tai-chi-interviews/gerda-geddes/
(  0) 0)
|
| [23] |
ROBINSON R.Tai Chi interview: Paul Crompton[EB/OL].[2018-08-25].https://taiji-forum.com/tai-chi-taiji/tai-chi-interviews/tai-chi-interview-paul-crompton/
(  0) 0)
|
| [24] |
ROBINSON R. An interview with Gary Wragg[J].
Tai Chi Chuan & Oriental Arts, 2011, 30(Winter): 18-24 (  0) 0)
|
| [25] |
SMITH R.
Martial musings:A portrayal of martial arts in the 20th century[M]. Pennsylvania: Via Media Publishing, 2013: 36.
(  0) 0)
|
| [26] |
International Tai Chi Chuan Association.Master Chu King Hung[EB/OL].[2018-08-25].http://www.itcca.com/en/europe
(  0) 0)
|
| [27] |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37-238.
(  0) 0)
|
| [28] |
ROBINSON R.Tai Chi interview: Dan Docherty[EB/OL].[2018-08-25].https://taiji-forum.com/tai-chi-taiji/tai-chi-interviews/dan-docherty-interview/
(  0) 0)
|
| [29] |
LOGAN B. Daniel in the dragon's den[J].
Traditional Karate, 1988, 2(2): 16-24 (  0) 0)
|
| [30] |
ROBINSON R. Linda Chase Broda:1941-2011[J].
Tai Chi Chuan and Oriental Arts, 2011, 30(Summer): 20-27 (  0) 0)
|
| [31] |
ROBINSON R. An interview with Faye Li Yi[J].
Tai Chi Chuan and Oriental Arts, 2013, 43(Autumn): 6-11 (  0) 0)
|
| [32] |
Chen Style Tai Chi Centre.Grandmaster Liming Yue[EB/OL].[2018-08-25].http://www.taichicentre.com/masterliming.php
(  0) 0)
|
| [33] |
The Tai Chi Union for Great Britain.Instructors[EB/OL].[2018-08-25].http://www.taichiunion.com/instructors/
(  0) 0)
|
| [34] |
JENNINGS G. Transmitting health philosophie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ist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the UK[J].
Societies, 2014, 4(4): 712-736 (  0) 0)
|
| [35] |
王俊杰, 王培勇, 徐坚, 等.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外太极拳运动研究热点与演化分析[J].
体育科学, 2012, 32(10): 77-84 (  0) 0)
|
| [36] |
马秀杰, 王伟. 太极拳国际研究动态分析: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研究[J].
邯郸学院学报, 2018, 28(1): 48-64 (  0) 0)
|
| [37] |
钟伶. 基于Web of Science的国际太极拳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4): 907-915 (  0) 0)
|
| [38] |
陆颖, 李洁, 肖斌, 等. 国外太极拳临床研究现状与思考[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3, 33(12): 1717-1721 (  0) 0)
|
| [39] |
WANG C, SCHMID C H, RONES R. A randomized trial of Tai Chi for fibromyalgia[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 363(8): 743-754 (  0) 0)
|
| [40] |
LI F, HARMER P, FITZGERALD K. Tai Chi and postural st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2, 366(6): 511-519 (  0) 0)
|
| [41] |
马秀杰, 姜传银, PaulBowman. 李小龙的文化遗产:第四届国际武术论坛学术综述[J].
体育与科学, 2018(5): 13-18 (  0) 0)
|
| [42] |
孟涛, 蔡仲林. 传播历程与文化线索:中华武术在美国传播的历史探骊[J].
体育科学, 2013, 33(10): 78-88 (  0) 0)
|
| [43] |
闫海军."文化走出去"十年大事记[EB/OL].[2018-08-25].http://www.chmeng.com/show-19-2238-1.html
(  0) 0)
|
 2020, Vol. 44
2020, Vol.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