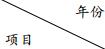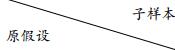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通过金融风险的溢出与传导机制、金融市场对各类冲击的放大与加速机制,金融体系显著改变了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与其后欧债危机的接踵爆发,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是引发了学界对“现代衰退”的重新认识与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深度反思。其中,研究金融冲击对实体经济的传导途径与影响机制,既是深入理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复杂关联机制、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与突破口,同时也是科学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金融监管措施的关键,因而是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经济结构的系统性调整阶段和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时期,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中之重。然而近年来中国地方债务危机、“钱荒”、股票市场“千股跌停”、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等异常事件频现,不仅阻碍了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与助推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为新时期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积下了隐患。因此,在实体经济下行与金融风险积聚的双重压力背景下,探索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变动特征和传导机制、检验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间的非线性交互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宏观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而且可以为完善应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监管措施、有效统筹“稳增长、防风险”的目标提供有益的经验支持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事实上,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理论探讨。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揭示了银行体系脆弱性与宏观经济周期的紧密联系,并指出其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实体经济恶化;Minsky(1982)在其“金融不稳定假说”中也把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波动主要归结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Bernanke et al.(1996, 1998)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并修改金融中性理论的前提假设后,金融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重要作用得以确立,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该理论指出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现实存在将显著放大或扩散金融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因而有效监测金融市场风险并将金融稳定纳入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框架是极为必要的。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各种统计和经济计量方法对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仍然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决定着金融市场外部运行环境的好坏,对金融体系风险承担水平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Engle and Rangel(2008)通过GARCH模型研究发现GDP增速降低、通货膨胀上升以及出口增长回落均将加剧股票市场的低频波动;Calmès and Théoret(2014)选取EGARCH模型衡量了宏观经济冲击对银行体系风险的影响,发现非利息收入对宏观经济冲击更为敏感;李麟、索彦峰(2009)基于VAR模型得出银行业不良贷款对GDP冲击产生负向响应,且在银行信贷亲周期性特征的作用下,系统性风险极易被触发;潘敏等(2012)通过GMM模型检验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负向(正向)的宏观经济冲击会使银行风险提高(降低);星焱(2014)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得出宏观经济增速趋缓会引致银行业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的增加;蒋海、陈静(2015)考察了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非对称性影响,发现银行风险在经济衰退期受经济波动影响更大;徐荣等(2017)建立基于有向无环图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和房地产价格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同期影响关系,特别是房价对金融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等等。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金融风险源于金融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扭曲、梗阻,不仅借助内部传导机制危及金融稳定,更会延伸至实体经济并致使其陷入衰退。例如Bullard et al.(2009)认为,系统性风险首先会作用于金融体系,进而波及到宏观经济,对经济稳定带来较大的冲击效应;Allen et al.(2012)发现银行体系内高系统性风险水平通过总的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Jin and Zeng(2014)认为银行风险变动会导致整体宏观经济活动的波动,且通过建立金融安全网和提高风险分担可以部分缓解银行风险冲击的不利宏观经济效应;陈守东等(2013)通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得出,金融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高速”与“适速”阶段表现出非对称性;陈雨露、马勇(2013)构建金融失衡指数用于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检验发现该指数领先于GDP与CPI的变动,证实了金融层面的失衡要先于宏观经济失衡的发生;郭永济等(2014)利用TVP-VAR模型考察了流动性过剩冲击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发现时变性取决于流动性增加的来源和宏观经济状态(经济周期、信贷周期、通货膨胀周期、货币政策立场等);王妍(2015)基于金融脆弱和金融压力指数,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系统具有周期性演变特征,并且金融不稳定对宏观经济具有长期预测能力;刘瑞兴(2015)基于金融压力指数与实体经济间的自回归模型得出中国金融压力对实体经济存在长期的逆向影响关系;等等。
除上述两种观点外,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探究金融风险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冲击与影响机制,得出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或者两者之间影响关系可能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而表现出阶段性差异与状态依赖特性的结论。例如Beltratti and Morana(2006)利用标普指数考察股票市场波动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尽管股票市场波动性也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产生影响,但宏观经济因素对股市波动的冲击作用更加显著;Liliana et al.(2014)则通过研究发现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表现出差异性特征,认为在宏观调控和政策设计时应着重加强对金融周期的监管;刘晓星、方淋(2014)利用PVAR模型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前后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冲击作用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表明:危机爆发使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间的联系变得十分紧密;发达国家系统性风险指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明显,而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指标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雷蕾、彭孙琥(2016)以CPI变动率反映价格稳定,考察其与金融压力指数的相关性,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时变性与非对称性特征。
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影响关系的理论分歧无疑会造成政府在政策制定或市场干预导向上的不确定性。而从现有相关实证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就两者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也远未达成一致。这除了检验方法不同或样本选择差异等方面的原因以外,仍有两处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一方面,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某一金融子系统风险(如股票市场、银行体系风险等)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及传导机制,而金融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既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又可能因自身运行特征以及风险传染途径的不同,在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机制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因而进一步考察并比较各金融子市场风险的变动规律、传递机制以及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必要的,不仅可以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之间的作用机制,而且有助于针对不同金融子市场的风险变动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定向调控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实现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精准防控。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在分析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影响作用时,对时变性、状态依赖性等非线性特征的考虑相对较少。事实上,金融市场的风险来源复杂多变,而且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固定系数模型很难揭示出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影响关系的阶段性差异或时变规律。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开放度不断提高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风险的传导机制及其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可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运用动态计量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检验,深入考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或市场环境下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之间的关联动态是极为有益的。
作为一种尝试与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拟在对货币市场、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风险进行测度并考察其传递关系的基础上,选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 将各金融子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统一的VAR系统中,通过有效捕捉系统中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考察不同的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的关联特征与影响动态。以期为深入理解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影响关系的时变规律,科学制定新时期宏观调控政策与金融监管措施、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双重稳定提供有益的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三、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评估及其传递关系金融市场风险的正确度量,是合理分析金融体系风险变动规律及其内部传导机制的基础,也是考察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关联动态的首要前提,因而是决定实证研究结果可靠性以及研究价值的关键。事实上,金融风险的来源复杂多变,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货币流动性的泛滥、资产价格泡沫的积聚以及银行体系运营状况的恶化,都将对整个金融和经济系统造成严重危害。为此,本节将在对金融市场风险评估方法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与经济的运行实际,选择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三方面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估,并以此考察各金融子市场风险的波动特征及其传递关系。
(一) 金融市场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考虑到货币市场作为资金流通与调配的场所,通过货币流动性的变动作用于宏观经济金融稳定;股票市场通过股价波动对实体经济产生溢出效应,进而影响宏观经济金融稳定;银行体系作为金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稳定性反映了金融系统的运行状况。故为度量金融市场风险,本部分将分别对货币市场流动性、股票市场泡沫以及银行体系风险进行测度,从而揭示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的变动状况与规律。
1. 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作为资金流通与调配的场所,货币流动性与经济运行对货币的实际需求是否匹配,对于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具有决定意义。一般来说,流动性过剩是引致通货膨胀甚至资产泡沫的重要原因,因而是货币市场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现有文献中关于流动性的测度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货币供求关系的角度对货币市场流动性进行衡量,将货币流动性过剩描述为流通的实际货币量与经济均衡状态下所需货币量的偏差。例如欧洲央行专家Polleit and Gerdesmeier(2005)提出的价格缺口法、真实货币缺口法、名义货币缺口法和货币过剩法等。另一类则主要考虑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将超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货币投放描述为超额货币供给。考虑到基于货币数量方程的货币需求函数较难准确估计,且对均衡货币量的定义存在主观基期选择等问题,可能造成较大误差;而货币流动性过剩作为一个相对指标,对流动性是否过剩的问题更应基于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判断。当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对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需的货币量进行合理确定较为困难,围绕货币流动性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关系设计出的流动性测度指标可能更具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择采用第二类方法,即根据M2增速-经济增速-当季CPI涨幅衡量货币流动性宽松程度,以反映货币市场的风险状态。所需计算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2. 股票市场文献中关于股票市场风险或泡沫的测度也有两类常见的方法。一类是从宏观角度,通过建立股票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计量模型,得到股指价值期望值,并将股指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额描述为股市的风险或泡沫。这类方法的缺点在于,模型中往往只能包含影响股市基本价值的部分宏观因素,因而导致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严重偏离市场的运行实际;第二类方法则是从微观角度,利用企业的财务信息,在测度企业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计算股票价格中泡沫成分的大小。此类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计算企业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的常用计算方法包括股利贴现模型(DDM)、自由现金流模型(FCE)和剩余收益模型(RIV)等等。其中,剩余收益模型考虑到股东机会成本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认为企业内在价值应是未来各期剩余价值(RIV)的贴现值与当期净资产的加总,因而相较于股利贴现模型和自由现金流模型更具合理性。因此,本文也将沿用Bernard(1995)、毛有碧、周军(2007)和吕江林(2012)等的做法,采用剩余收益模型对股票市场泡沫进行测度。
具体地,基于剩余收益模型(FO模型,Feltham-Ohlson Model),企业的平均内在价值IvtVt可表述为:
| $ \begin{array}{l} {V_t} = {B_t} + \sum\limits_{i = 1}^\infty {\frac{{R{I_{t + i}}}}{{{{\left( {1 + {r_t}} \right)}^i}}}} = {B_t} + \sum\limits_{i = 1}^N {\frac{{\left( {RO{E_{t + i}} - {r_t}} \right){B_{t + i - 1}}}}{{{{\left( {1 + {r_t}} \right)}^i}}}} \\ \;\;\;\; = {B_t} + {B_t}\left( {RO{E_t} - {r_t}} \right)\sum\limits_{i = 1}^N {\frac{{{{\left( {1 + RO{E_t} - {r_t} - {k_t} \times RO{E_t}} \right)}^{i - 1}}}}{{{{\left( {1 + {r_t}} \right)}^i}}}} \end{array} $ | (1) |
上式中,rt是第t期的无风险利率;Bt是第t期企业加权平均每股净资产;EPSt是第t期企业加权平均每股收益;RIt是第t期企业的剩余收益;ROEt为第t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且ROEt=EPSt/Bt-1;在考虑净剩余关系下,kt为第t期上市公司平均派息率;剩余收益预测期限为有限的N期,即认为N期后剩余收益为0,本文假设N为3年。
由企业平均内在价值Vt得到企业平均合理市盈率Ivt=Vt/EPSt,即可将股市泡沫定义为实际市盈率Ipt与合理市盈率Ivt之差,即ΔIt=Ipt-Ivt,并将泡沫度定义为ht=ΔIt/Ivt,作为股票市场风险的评估依据。上述计算过程中的无风险利率以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近似替代,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及企业实际市盈率均以沪深各股市值为权重进行加权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数据库(http://www.resset.cn)。
3. 银行体系银行体系风险的评估方法较多,文献中常见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基于资产负债数据对风险进行测度,包括KLR信号法、人工神经网络法、STV模型、网络模型法以及运用统计的加权方法(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建立综合指数等。二是基于股票债券市场数据,围绕着市场风险展开评估,其中条件在险价值CoVaR、边际期望损失MES和系统期望损失SES应用较广,包括ARCH模型、多元GARCH模型、CoRisk模型和EVT方法等。三是针对多市场数据的风险度量方法,这类方法主要集中于分析跨市场相关性的危机联合概率(JPoD)模型与未定权益分析(CCA)模型等。
综合比较三种度量方法,虽然当前测度系统性风险较前沿的研究方法是运用市场数据、通过压力测试、违约率等方法测度银行系统性风险,但从适用性角度来看,CoVaR和MES等方法更适合于评估某一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而基于资产负债表的风险衡量方法指标简单且易获得,反映的信息较为全面,更适合对银行业整体风险进行直观简明的度量分析,且IMF(2009)也曾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基于资产负债表的指标可作为衡量系统性风险的主要依据。综上考虑,本文将采用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综合指数法对银行体系风险进行测度。
具体地,本文将从资本充足状况、流动性状况、资产质量状况以及盈利性状况四方面选取相应指标,构建银行体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银行体系风险进行考察,各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合理确定,权重分配情况如表 1所示①。
| 表 1 银行体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分布 |
① 本文综合考虑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及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来构建银行体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在权重确定过程中,指标间的两两重要性程度主要依据Satty九级标度法并综合参考了寿晖、张永安(2013)、沈悦、亓莉(2008)及王伟(2013)等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赋值。
对各项指标分别选取18①家样本银行的季度平均值,依据指标映射法②,将各指标具体数值映射到百分制下的分值(区分正向指标及反向指标,其中正向指标的指标数值越大,所得分值越高),对所有指标得分值进行标准化后,按相应权重进行加权得到样本期内各季度银行体系风险的评估结果。各样本银行相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http://www.gtarsc.com)、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官方网站。
① 本文结合数据可获取性,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中选取了以下18家银行作为代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
② 指标映射的具体做法可参见中国银监会银行风险早期预警综合系统课题组(2009)、寿晖、张永安(2013)及王伟(2013)等。
(二) 货币市场、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的风险评估结果基于上述选定的评估方法,本文运用EViews8.0与SPSS22.0软件对2001年1季度至2016年4季度之间各金融子市场的风险进行了测度,并经季节调整与标准化处理后,得到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的风险评估结果如图 1所示。

|
图 1 各金融子市场的风险评估结果 |
表 2中列出了图 1中各序列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 2中可看出,虽然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在整个样本期内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态势,但三者的均值都小于0,表明我国的金融风险基本处在可控的水平内。股票市场风险的标准差最大,这正与我国股票市场投机性较强、易受外部事件影响等特征相符,而货币流动性的波动则相对较小。从分布特征来看,股票市场风险分布呈现出尖峰厚尾特征,并且股票市场风险和银行体系风险分别表现出明显的右偏和左偏特征。此外,我们可观察到各金融子市场风险的极值基本均出现在2005至2009年附近,即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金融风险的积聚既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而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又可能导致各金融子市场风险的状态也随之发生相应的不利转变。
| 表 2 各金融子市场风险序列的描述性统计 |
结合图 1中货币市场风险的变化情况来看,中国近年来货币市场共有三段时期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风险,分别是2003年,2005年下半年至2006年上半年,以及2009年。这三段时期较高的货币流动性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随后经济过热或物价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当然,货币市场流动性不足也会对宏观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例如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为应对物价急剧攀升而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流动性明显降低,而后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影响下,货币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并降至样本期内的最低点,流动性的短缺使得危机期间实体经济雪上加霜,一些原本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较高的中小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4万亿刺激计划和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下,2009年流动性急剧上升,货币市场风险明显增加。2010-2011年央行再启紧缩性货币政策,过剩的流动性得以逐步回收。进入新常态时期以来,中国货币政策趋于稳健,货币流动性在中低水平间徘徊波动,呈现温和收紧趋势,货币市场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从股票市场的风险变化情况来看,在2006-2007年、2014-2015年中国股市出现剧烈震荡的两段时期内,股票市场风险明显高于其它时期。2001年到2005年初股市风险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此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利好消息和大牛市的出现使得股市投机性泡沫盛行,特别是在2007年我国股票市场处于最为繁荣的时期,市场投机追涨现象严重,股市风险急剧增加;金融危机爆发后,股票市场泡沫破灭,股票市场进入调整阶段,虽有较频繁的波动,但股市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而在2014-2015年,中国股市再次经历了泡沫加速形成、股市迅速繁荣以及泡沫破灭、股指持续下跌的全过程。2016年起,股票市场处于相对平稳状态,市场风险维持在中低水平。
银行体系在2007-2008以及2010末至2012年两段时期呈现出较高的风险水平。2001年到2006年间,银行体系运行相对平稳,风险基本处在较低水平。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水平在2007-2008年间迅速上升,银行体系脆弱性显著增加。随着在对银行业的防御性救助措施以及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回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银行体系风险在2009年一度明显回落。但自2010年末开始银行体系风险再次跃至高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爆发等国内外复杂经济金融形势的冲击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危机后国内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持续高增长的信贷规模引致信贷风险升高密切相关。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实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银行同业竞争加剧,同时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推进以及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表外业务发展迅猛,银行体系风险逐渐累积显现。随着央行开始大力清理表外业务,并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限制其过度膨胀,2015年起银行体系风险表现出回落趋势。
对整体进行分析,首先从风险变动的趋势来看,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之间表现出一定趋同性:各金融子市场风险在经济平稳时期的变化均相对较为缓和,而在经济趋热或衰退等非平稳时期(如2003-2004年局部过热、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则表现出不断积聚和集中爆发的特征。其次,各子市场风险之间也呈现出一定差异性:虽然在某些阶段金融子市场风险之间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态势,波动的拐点和升降过程相继出现,而在某些时段其各自的风险强度、波动特征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可见,作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的变动在不同时期既存在相互影响的关联性,又具有一定差异性。
(三) 货币市场、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风险的传递关系为进一步探究金融风险的内部传导关系及其变动规律,本节根据2001-2016年间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基于非重叠三年窗口将样本划分为5个时段,分阶段计算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整理后的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 表 3 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之间的时差相关分析 |
由表 3可知,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滞,并且其传导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显著差异。就各市场的先行滞后关系来看,2001-2006年期间,货币市场流动性风险均先行于股票市场风险与银行体系风险;2007-2012年期间,银行体系风险先行于货币市场风险与股票市场风险;2013-2016年期间,货币市场风险再次先行于股票市场风险与银行体系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2001年以来,大部分时期货币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均先行于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风险,只有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货币市场风险才滞后于银行体系和股票市场风险。可见中国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推动特征,而银行体系风险和股票市场风险的积聚是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爆发的集中体现与重要源泉,尽管危机期间政府运用货币政策等手段注入流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控金融风险,但实体经济的衰退使得市场流动性难以有效吸收,从而可能间接导致货币市场流动性风险上升。
为了验证不同时期各金融子市场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与传递影响,我们进一步运用经典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货币市场、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风险之间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存在因果关系。为了避免样本长度过小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误,我们将样本大致均匀地划分为金融危机前(2001-2005)、金融危机期间(2006-2010)、金融危机后(2011-2016)三个阶段,分别检验了各金融子市场风险之间滞后1-6阶的因果关系,如表 4所示。
| 表 4 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从各金融子市场风险之间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来看:2001-2005年期间,“货币市场风险非银行体系风险的Granger原因”、“股票市场风险非银行体系风险的Granger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几乎均被显著拒绝;2006-2010年期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银行体系风险非货币市场风险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1-2及4-6期的设定下均被拒绝,“股票市场风险非银行体系风险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2-4期的设定下被拒绝;2011-2016年期间,“货币市场风险非银行体系风险的Granger原因”再次在10%的显著性水平被拒绝,“银行体系风险非股票市场风险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2-6期的设定下被显著拒绝。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不仅与前述时差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大体一致,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市场风险之间传递关系的阶段性差异:金融危机以前,货币市场风险和股票市场风险是引起银行体系风险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传导,并最终引致货币市场的流动性风险;而中国自金融危机后步入新常态经济以来,货币市场风险引起银行体系风险继而向股票市场传导,是金融子市场之间风险传导的主要途径。
四、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的关系金融市场风险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传递和影响关系,这也暗含了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显著的阶段差异或状态依赖性。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基于前述各金融子市场风险的测度结果,以宏观经济一致合成指数(CI) ①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景气的代理指标,运用动态计量方法深入考察不同时期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的复杂影响关系及其时变规律,以期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金融风险防控措施的科学制定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①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使用月度数据计算出季度平均值,并为了消除量纲影响,将(原始数据-100)/100后的值作为最终模型使用数据。
近些年来,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成为了分析经济系统中变量之间时变关系的常用工具。该模型作为传统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拓展形式,一方面保留了VAR系统将所有变量均视为内生变量的优点,为解决变量之间的同时性问题、分离各变量对自身和其他变量冲击的动态反应提供了有用框架;另一方面放松了模型系数矩阵和扰动项协方差矩阵非时变的约束,可以有效捕捉系统中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而对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变特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邓创、席旭文,2013)。鉴于此,为考察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影响关系的时变特征,本节构建了一个由货币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体系风险和宏观经济一致指数组成的四变量TVP-VAR模型,并参照无约束VAR系统下的AIC准则将模型滞后阶数选定为2阶,在MATLAB软件下借助贝叶斯推断下的马尔科夫蒙特卡罗方法(MCMC)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Nakajima et al., 2011)。为节省篇幅,本节省略了对模型计算步骤和参数估计结果等的详细描述,直接运用时变脉冲响应函数依次模拟出不同时期金融市场风险变动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金融市场风险的冲击影响,以考察和分析不同时期两者之间的时变关联特征。
(一) 金融市场风险波动对宏观经济景气的时变影响首先,我们考察货币市场、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图 2中分别描述了宏观经济景气对三个金融子市场风险一个标准差大小冲击的时变响应。

|
图 2 宏观经济景气对各金融子市场风险冲击的时变响应 |
从图 2(a)中描述的宏观经济景气对货币市场流动性冲击的时变响应来看,货币市场流动性风险的增加一开始均对宏观经济景气产生了负向冲击,但在第4期左右便开始转为正向影响。并且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增加对宏观经济景气产生的正向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尽管货币市场风险的增加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具有抑制效应,但货币流动性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渠道和基本手段,仍然可以对宏观经济景气起到有效地逆风向调控效果。即在宏观经济繁荣甚至趋于过热时,收紧流动性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在宏观经济下行阶段,提高货币流动性则可以有效缓解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从图中可以看到整个样本期间内,2010年左右货币市场流动性增加对宏观经济景气的正向冲击最为明显,这与中国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的运行现实与调控实践也是极为相符的。2009年开始中国出台了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系列救市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后尽管增加了货币市场风险,但仍然对宏观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可见,在密切监控货币市场风险的前提下,合理提高货币流动性对于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发展仍然是极为有益的
从图 2(b)来看,股票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在金融危机前后同样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危机前,中国股票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规模相对较小,股票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大致呈现出在零线附近上下摆动的微弱变化态势;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股票市场风险增加对宏观经济景气的抑制作用开始迅速显现并显著增强。尽管随后股票市场进入调整阶段并持续处于偏冷状态,小牛市和小熊市交替出现,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冲击也呈现出弱化趋势。但自2014年初起,中国股市经历了迅速繁荣而后持续下跌的全过程,市场风险积聚对宏观经济景气的负向影响不仅在程度上再次强化,且达到最大响应的滞后期也明显缩短。由此可见,有效防控股票市场风险积聚以降低其对宏观经济景气的负向冲击,仍然是新时期金融市场改革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
银行体系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在金融危机前后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如图 2(c)所示。在整个样本期内,银行体系风险增加在一开始即对宏观经济景气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影响,并且这种负向冲击同样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明显增强。另外,从图中可以发现,2003年下半年、2007-2008年与2014-2015年三个时期,银行体系风险增加对宏观经济景气的负向冲击影响尤为明显。结合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运行实际来看,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盲目投资等系列问题,导致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银行业不良贷款急剧增加;2007-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国内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与国外金融危机传导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银行体系脆弱性凸显;而2014-2015年期间,股票市场又一次经历剧烈震荡,并且银行体系也出现了同业业务过度膨胀、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等系列问题。可见,在经济处于过热或衰退的不稳定阶段,不仅银行体系的风险急剧增加,而且其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也更为显著。
综上分析,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变动的冲击影响既有相似的时变特征又有显著的市场差异。首先,各金融子市场风险增加均在一开始即对宏观经济景气产生了负向的冲击影响,并且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明显增强。其次,金融市场风险变动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影响作用表现出明显的状态依赖性,冲击程度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均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即在经济运行较平稳时期,冲击程度和持续时间相对较小;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或趋热的不稳定阶段,金融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表现出更为强烈和持久的影响。最后,就不同金融子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影响差异而言,银行体系风险与货币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要大于股票市场风险的影响,但货币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产生不利影响的持续期相对较短,并且流动性的合理增加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而相比之下,银行体系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负向影响更为深远。可见,新时期加强对金融市场风险特别是银行体系风险的防控,对于降低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提高宏观经济反周期调控效果十分关键。
(二) 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时变影响为考察样本期内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金融市场风险冲击影响的时变特征,我们同样绘制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冲击的响应动态,如图 3所示。

|
图 3 各金融子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冲击的时变响应 |
由图 3(a)来看,在整个样本期内,宏观经济景气冲击对货币流动性基本表现为正向影响,表明在经济运行状况良好时,实体经济与货币流动性表现出较好的协动性,宏观经济景气好转有助于推动流动性水平的提升;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此正向影响明显强化,这与危机时货币流动性收紧,而宏观经济的下滑则会加剧流动性紧缩态势的事实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流动性过剩出现时(如在2006年经济趋热以及危机时4万亿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景气对货币流动性的冲击影响迅速转为负向。而2013年后,宏观经济景气冲击对流动性的影响逐步减弱并趋于平稳。可见,当前经济景气变动对流动性的影响已经明显弱化,货币流动性紧缩大多来源于其内生性紧缩机制,体现在M2增速与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之间的差额扩大,呈现“宽货币、紧融资”的局面。
图 3(b)表明,在整个样本期内宏观经济景气冲击对股票市场风险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经济形势好转(衰退),股票市场风险下降(上升)。特别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股票市场风险的这一负向影响明显增强。因此,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的同时,对股票市场风险产生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尽管中国股票市场运行机制仍然很不完善,有待进一步地调整和改革,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稳定仍然是支撑股票市场平稳运行的前提和重要基础。
从图 3(c)来看,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银行体系风险同样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冲击影响。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并且得益于银行股份制改革持续深化和政策剥离等措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实现双降、信用风险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该期间宏观经济好转对银行体系风险的抑制作用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而从2007年开始,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体系风险的负向冲击影响有所减弱,直至2012年左右这一负向冲击才开始显著增强,并且滞后期明显缩短。中国经济自危机后步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一致指数总体上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体系改革措施,但宏观经济景气下行与金融体系风险积聚并存的现象依然持续存在。另外,对比不同时期的脉冲模拟可以发现,虽然宏观经济景气好转对银行体系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影响程度上要明显强于宏观经济景气恶化的不利影响,但银行体系风险对经济景气恶化冲击的反应更为迅速。
综上分析,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金融市场风险的冲击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显著的阶段性差异。具体表现为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货币市场流动性风险的正向影响减弱、对股票市场风险的负向影响显著增强、对银行体系风险的负向冲击影响更为迅速。另一方面,比较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各金融子市场风险冲击影响的差异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股票市场风险的影响最为迅速,其次是银行体系风险,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仍然是有效降低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风险的重要途径。这些检验结果不仅证实了对宏观经济景气与金融市场风险之间关系进行时变分析的必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风险监管提供有益的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本文分别从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及银行体系三方面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进行测度,并通过时差相关分析和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不同时期各金融子市场风险的演变动态及其传导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市场风险的产生与传导呈现出较明显的非线性波动特征,一方面各金融子市场风险均表现出经济平稳时期的较缓和变化、非平稳时期快速积聚与集中爆发的非线性特征;另一方面,各金融子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目前,货币市场风险引起银行体系风险继而向股票市场传导,是金融子市场之间风险传导的主要途径。
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深入探究了各金融子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之间的关联动态。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与复杂,并且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与金融市场风险积聚现象并存,为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故基于两者间双向影响动态的研究结果不仅可获取以下三方面的重要结论,从而揭示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也分别得到若干有益的政策启示:
首先,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的关系在“良性循环”和“恶性螺旋”之间呈现出阶段性切换,存在明显的状态依赖与非对称性特征。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尽管在2003年以及2006年左右,宏观经济局部过热,金融体系中各类潜在风险开始集中显现,但金融风险的上升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加之适时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措施,在宏观经济回归平稳的同时,金融市场风险也随之回归低位。可见在宏观经济景气持续向好的阶段,宏观经济景气与金融市场风险之间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宏观经济形势向好发展,推动货币流动性上升、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风险下降,虽然流动性的增加一开始会对宏观经济景气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将很快转变为对宏观经济景气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银行体系与股票市场风险的降低也明显有助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好转,因而最终呈现出金融稳定与经济向好的良性循环动态。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危机期间,国内外金融经济环境的动荡使得金融市场最先遭受重创,通过金融体系内部传染与扩散效应,最终表现出金融体系风险全面上升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而宏观经济景气的恶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风险,形成“金融市场动荡—经济景气下行—金融风险上升”的恶性螺旋。这种宏观经济波动与金融市场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及反馈相比于危机前的良性循环,不仅在冲击程度上更为显著,而且在影响时间上也更加持久,即经济衰退时形成的恶性螺旋与经济向好时表现出的良性循环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市场风险防控两手都要抓,在密切监测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的同时,应特别注重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与金融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运用,谨防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之间出现恶性螺旋。
其次,由于不同金融市场风险之间存在异质性与传递影响关系,因而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差异。从金融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来看,银行体系风险与货币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冲击影响要大于股票市场风险的影响,但货币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产生不利影响的持续期相对较短,并且流动性的合理增加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来看,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对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股票市场风险的影响相对更大。不同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之间关系的差异,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程度和传递关系不同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中国银行体系一直在金融系统处于主导地位,也是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传导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股票市场经过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在优化资源配置与引导市场预期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而货币供给尽管一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风向标,但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加之信贷需求结构性问题以及政策监管滞后等问题的存在,社会融资结构和融资渠道发生了系统性变化,这不仅加大了市场风险的识别与防控难度,而且也使得货币市场流动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表现出弱化趋势。因此,新时期加强对金融市场风险特别是银行体系和股票市场风险的防控,对于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传导冲击、兼顾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尤为关键。一方面,应在积极创新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继续坚定不移地落实金融去杠杆工作,积极引导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回归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与支撑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创新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针对不同金融市场及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特征,运用差异化的定向调控和监管政策、持续推进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
最后,金融市场风险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发生了系统性转变。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特别是金融风险冲击对宏观景气变动的影响明显增强。这不仅表明,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影响渠道增多,宏观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联愈发紧密与复杂;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决策机制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政府决策主导市场的运行模式,即政府提出总的经济发展目标后,各级市场和相关部门围绕政府预期进行部署或制定相关调控政策,引导市场参与者调整其市场预期及市场行为,进而对金融与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这种以政府预期引导市场预期的决策机制下,金融体系的波动往往滞后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传导或反馈作用相对有限,难以有效发挥其“晴雨表”功能。而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宏观经济与金融之间的传导关系日益复杂,特别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以及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传导冲击引起了许多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警惕。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开始更多地加入对金融市场稳定性与市场预期的考虑,并根据市场预期适时调整政府预期。显然,这种基于市场预期调整政府预期的决策机制更多地考虑了金融体系的实际运行条件与稳定性要求,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作用。事实上,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与金融市场风险积聚现象并存,为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监管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为严峻的挑战,既要防止金融体系脱离实体经济成为自我服务的“空转”系统,又要积极提振市场活力以推动宏观经济回暖向好。面对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市场监管的两难选择,积极推进政府决策机制和调控方式的创新与转变是极为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监管,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仍应继续完善“基于市场预期适时调整政府预期”的决策机制,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晴雨表”功能,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并结合不同金融经济环境下金融市场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的影响特征,协调运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与金融监管措施,以实现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双重稳定与协调发展。
| [] |
陈守东、王妍、唐亚晖,
2013, “我国金融不稳定性及其对宏观经济非对称影响分析”, 《国际金融研究》, 第 6 期, 第 56–66 页。 |
| [] |
陈雨露、马勇,
2013, “构建中国的'金融失衡指数':方法及在宏观审慎中的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第 1 期, 第 59–71 页。 |
| [] |
邓创、席旭文,
2013, “中美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时变特征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第 9 期, 第 10–20 页。 |
| [] |
郭永济、李伯钧、金雯雯,
2014, “时变框架下中国货币流动性的影响研究:1992-2012”, 《当代经济科学》, 第 1 期, 第 1–11 页。 |
| [] |
蒋海、陈静,
2015, “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金融经济学研究》, 第 3 期, 第 46–57 页。 |
| [] |
雷蕾、彭孙琥,
2016, “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2002-2015年数据实证研究”, 《南方经济》, 第 2 期, 第 106–117 页。 |
| [] |
李麟、索彦峰,
2009, “经济波动、不良贷款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国际金融研究》, 第 6 期, 第 55–63 页。 |
| [] |
刘瑞兴,
2015, “金融压力对中国实体经济冲击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 6 期, 第 147–160 页。 |
| [] |
刘晓星、方琳,
2014, “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稳定:影响机制及其实证检验”,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第 5 期, 第 65–77 页。 |
| [] |
吕江林、曾鹏,
2012, “中国股票市场泡沫度量——基于流通股内在价值分析”,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第 1 期, 第 78–86 页。 |
| [] |
毛有碧、周军,
2007, “股市泡沫测量及性质区分”, 《金融研究》, 第 12 期, 第 186–197 页。 |
| [] |
潘敏、张依茹、李睿,
2012, “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基于股权结构异质性的视角”, 《财贸经济》, 第 10 期, 第 57–65 页。DOI:10.3969/j.issn.1005-913X.2012.10.032 |
| [] |
沈悦、亓莉,
2008, “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及监测分析”,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 第 139–143 页。 |
| [] |
寿晖、张永安,
2013, “基于AHP-熵值法商业银行体系风险指标预警研究——来自2003-2012年数据”, 《华东经济管理》, 第 10 期, 第 44–49 页。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3.10.010 |
| [] |
陶玲、朱迎,
2016, “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度量——基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研究”, 《金融研究》, 第 6 期, 第 18–36 页。 |
| [] |
王维国、王际皓,
2016, “货币、银行与资产市场风险状况的识别——基于金融压力指数MSIH-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第 8 期, 第 71–81 页。 |
| [] |
王伟,
2013, “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危机预警系统构建与警情分析——以A股上市银行为例”, 《中国经济问题》, 第 1 期, 第 92–99 页。 |
| [] |
王妍,
2015, “金融不稳定能够预测未来的宏观经济表现吗”, 《数量经济研究》, 第 1 期, 第 58–70 页。 |
| [] |
星焱,
2014, “宏观波动、市场冲击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基于中国92家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 《金融评论》, 第 6 期, 第 12–25 页。 |
| [] |
徐荣、郭娜、李金鑫、何龄童,
2017, “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动态机制研究——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分析”, 《南方经济》, 第 11 期, 第 1–17 页。 |
| [] |
中国银监会银行风险早期预警综合系统课题组,
2009, “单体银行风险预警体系的构建”, 《金融研究》, 第 3 期, 第 39–53 页。 |
| [] |
Allen L., Bali T.G. and Tang Y., 2012, "Does Systemic Risk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Predict Future Economic Downturn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5(10), 3000–3036.
|
| [] |
Beltratti A., Morana C., 2006, "Breaks and Persistency:Macroeconomic Causes of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31, 151–177.
DOI:10.1016/j.jeconom.2005.01.007 |
| [] |
Bernake B., Gertler M. and Gilchrist S., 1996,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1), 1–15.
DOI:10.2307/2109844 |
| [] |
Bernake, B., Gertler, M. and Gilchrist, S., 1998, "The Financial Acceleratio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NBER Working Paper, No. 6455.
|
| [] |
Bernard V., 1995, "The Feltham-Ohlson Framework:Implication for Empiricist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1, 733–747.
DOI:10.1111/care.1995.11.issue-2 |
| [] |
Bullard J., Neely J.C. and Wheelock C.D., 2009, "Systemic Risk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A Prim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91, 403–417.
|
| [] |
Calmès C. and Théoret R., 2014, "Bank Systemic Risk and Macroeconomic Shocks:Canadian and U.S.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40(1), 388–402.
|
| [] |
Engle F.R., Rangel G.J., 2008, "The Spline-GARCH Model for Low-Frequency Volatility and Its Global Macroeconomics Caus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1(3), 1187–1222.
DOI:10.1093/rfs/hhn004 |
| [] |
Fisher I., 1933, "The Debt 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 Econometrica, 1, 337–357.
DOI:10.2307/1907327 |
| [] |
IMF, 2009,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 IMF Working Paper, April.
|
| [] |
Jin Y., Zeng Z., 2014, "Banking Risk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48, 350–360.
|
| [] |
Liliana D., Veronica M.C. and Lonela M.O., 2014, "Financial cycles-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Financial Crises". Management Intercultural, 2(31), 263–274.
|
| [] |
Minsky, H. P., 1982,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Capitalist Proces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Economy, in Financial Crisis: Theory, History and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38.
|
| [] |
Nakajima J., Kasuya M. and Watanabe T., 2011, "Bayesian Analysis of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5(3), 225–245.
|
| [] |
Polleit, T. and Gerdesmeier, D., 2005, "Measures of Excess Liquidity", Frankfurt School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