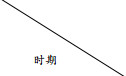产权(Property Rights),是人类社会持存之根本,东西方皆然。“没有人能够怀疑,划分财产且稳定其占有关系的惯例,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建立人类社会所最为必要的条件,并且当人们就订立和遵守上述规则达成同意之后,对于建立一个和谐与和睦的完善社会来说,便几乎没有多少事要做的了”(Hume, 2007, pp. 315-316);“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①
① 本文所用传世文献,其中儒家经典一般均参考中华书局版《十三经注疏》,非儒家之诸子百家经典一般均参考中华书局版《新编诸子集成》。
何谓产权?经济学界的标准解释可参照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产权词条(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008, vol. 6, p. 696),“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实施的选择某种经济物品使用用途的权利。私有产权是归属于个人的产权,它可以通过转让以换取对其他物品类似的权利。私有产权的效力取决于强制实施的可能性及为之付出的成本,这种强制有赖于政府、日常的社会行动以及通行的伦理和道德规范”。
在法律上,产权通常对应的概念是“所有权”(Ownership),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除了上述二者标准化定义之外,也可参考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那类形象化的界定和阐述,“产权是一个概念,像能量一样,无法直接体验。纯粹的能量看不见摸不着。同样也没有人能看见产权。只能通过能量和产权产生的效应,来体验产权”(de Soto, 2000, p.47)。所以德·索托将产权解析为六种效应(de Soto, 2000, pp. 47-62):(1)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2)用单一系统整合分散的信息;(3)使人权责明晰(accountable);(4)使资产便于交换(fungible);(5)建立人际关系网络;(6)保护交易。
然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产权形态似乎无法融入上述任何一种解释之中。
通过简单对比有关产权现象的史料记载,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困难。①
① 从法律意义上而言,现代财产权利包括物权--不动产和动产、债权、专利权以及其他财产权利。但是当学者们在讨论传统社会时,通常会集中于“土地权利”(即不动产权利的一部分),这与传统社会的特殊性有关。在传统社会,由于技术、法制和观念等主客观因素限制,对行为人而言土地是最为重要的财产。所以在本文中,如无特殊指明,“产权”一词的具体指称对象一般为地产。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产权性质就逻辑上而言可以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利,尽管某些产权形式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
首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北山》),这是传世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语句,与此相近的表达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左传·昭公七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表述通常被解读为传统社会是“君主私有制”。②
② 当然,亦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公有制或者国有制。关于学者观点的争论,详见本文第二节。
其次,“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商君书·定分》);“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慎子·逸文》)。这两段表述则显示出很强的财产私有意味,而且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现存铭文中有不少记录了关于土地交易和纠纷争讼的案例,较具代表性的如倗生簋(集成4262),③记录了一桩在西周官员见证下发生于格伯和倗生之间的土地交易,并铸器以“用典格白(伯)田”。④按照现代经济学和法学理解,土地既然能够合法交易,①那么至少具有事实上的“私有产权”性质②。
③ 有关金文资料本文参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简称《集成》,后附编号为该铭文在《集成》中的编号。
④ 铭文中用“典”字,表明该青铜器具有档案记录的性质,参见李峰(2010,第20页)。根据李朝远(1990)的考证,面世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涉及土地交换的有八件,除了已经提及的倗生簋以外,还有裘卫盉(集成9456)、九年卫鼎(集成2831)、五祀卫鼎(集成2832)、曶鼎(集成2838)、比鼎(集成2818)、比盨(集成4466)和散氏盘(集成10176)。但依笔者所见,其中曶鼎记载的是曶和匡季之间盗取庄稼的纠纷,要求用五“田”作赔偿,不直接涉及土地交易,不过仍反映土地产出物之归属问题。其他七件则与土地交换、土地纠纷以及周王分封土地冲突相关,且与此类内容相似的还包括比蓋(集成4278)。
① 这些铭文记载的交易中均有周王本人或周王代理人(政府官员)见证,而非私相授受。
② 例如赵冈、陈钟毅(2006a,第16-18页;2006b,第32页),就持这种观点,认为土地既然能自由买卖,而且有契为证,就是私有产权的最好证据。但是他们考证的土地买卖始于战国后期,认为秦国商鞅变法正式将土地买卖合法化。最新的史料证据显示出土地的合法转让至少自西周起就已出现,尽管当时的土地交换仅限于贵族之间,且需要周王或周王的代理人参与为要件。
再次,同样是《商君书》中记载,“故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商君书·算地》);“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商君书·徕民》)。其中“为国分田”、“制土分民”这些词句都是国家授田予民的明确表述,这就表明至少在《商君书》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末期--出现了“公有制”或“国有制”的产权形态。③出土文献亦有“授田”制度的证据,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有载,“入顷芻稾,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墾)不豤(墾),顷入芻三石、稾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1990, 释文第21页);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田法》有“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的记载(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1985, 释文第146页)。这就印证了在传统社会,国家确实对土地产权拥有控制权--至少当时的法令是如此规定。④
③ 后世传世文献中还有对上古社会“授田”制度的描述,例如《汉书·食货志》言,“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但是这类论述缺少可靠的旁证,暂且存疑。
④ 至于这种控制权的实际效果,另当别论。
有鉴于此,目前在探讨我国传统社会产权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两类趋势:一类是移植成熟的现代产权理论来梳理中国社会的产权史料与现象,例如曹树基等(2010)、龙登高等(2013)的研究;另一类则是承继黄宗智(2005a、2005b)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不适用于西方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具有典型的西方特色和形式,必须完全从中国经验出发另创中国式理论,陈锋(2012;2014)、桂华、林辉煌(2012)以及谢小芹、简小鹰(2014)等人的研究即是如此。
如何认识传统中国社会财产权利的性质,⑤是本文的主旨。
⑤ 有必要指出,本文中所指的“传统”和“现代”,并非时间序列意义上的区分--例如1911年之前是“传统社会”之后是“现代社会”之类,而是一种制度意义上的划分,因此尽管本文探讨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产权”,但并不意味着当代我国社会中就不存在类似的产权事态。
笔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产权首先是一个定性问题,而要进行定性分析既要避免陷入生搬硬套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产权理论的窠臼,也要避免盲目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必须从特殊经验中去发掘一般性事实的存在。因为就经验而言,每一个社会皆有其特殊性,与社会中每个行动主体利益攸关的产权现象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看似千差万别的表象背后就不存在某种共通的逻辑。本文就是希望通过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来寻找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产权性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节中笔者将对到目前为止有关传统中国社会产权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简单梳理;并在第三节中结合具体的经验材料--清代闵北土地买卖文书--来反思这些文献中所反映的观点;然后在第四节笔者将解析传统社会产权现象中的一般性事实,并以此为依据界定这类财产权利的性质;最后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余论。
二、 文献据笔者管窥所见,我国学界有关传统中国社会财产权利性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是围绕着史学界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展开的。①在这次讨论中,对于传统社会产权属性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类观点。②一类观点认为我国传统社会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如侯外庐(1954)就持有一种“王有制”的观点,认为“君王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而韩国磐(1959)从国家授田原则出发,认为这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度。第二类观点则认为传统社会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其中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种私有制是“地主私有制”,如束世澂(1957)、高敏(1960)、张传玺(1978)和胡如雷(1979)等学者都认为传统社会存在土地兼并问题、土地买卖现象,这些都说明当时土地并非国有或君主所有,而是一种地主所有制形式;而侯绍庄(1957)和刘毓璜(1960)等学者则认为除了存在地主所有制外,我国小农经济中长期存在大量的自耕农,因此“自耕农小土地私有制”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① 严格来说当时所讨论的“所有制”和我们今日所言的“产权”还是有所区别的,但主要是受时代因素所限,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② 启循(1979)对当时有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作了简要的综述,文中将各家观点归为三类,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从产权属性来看都属于“私有制”,在本文中归为一类。
最终,这场讨论奠定了接下来数十年间学界有关我国传统社会产权形态认知的主流观点,即“地主私有制”(张越,2016)。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秦晖所主张的“关中模式”--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秦晖、金雁, 2010, 第44页),③持有的就是自耕农“小私有制”观点。
③ 本文引用的文献--《田园诗与狂想曲》,是秦晖和金雁于2010年出版的新版,但是“关中模式”的观点早在80年代就已经提出。
不过王家范(1999a、1999b)开始反思上述理论,这是学界有关传统社会产权性质讨论的第二个时期。王家范先生认为,过去我国史学界所认识到的那种传统社会的“私产”现象,实际上只是“私人占有”,因为在皇权之下,没有任何个人--豪强地主或自耕农--能够防止权力对权利的掠夺。缺乏制度保障的“私产”不能称为“私有制”,其实质仍然是“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王家范,1999b)。程念祺(1997、1998、2000)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土地国有制,但并不稳定,因为“中国古代的土地国有制,强调的是国家主权及其意识形态。它在本质上,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从属于国家主权,把土地制度纯粹地意识形态化。而它所忽视的,是制度制定的法理,以及必要的制度安排与组织”(程念祺,1998)。李朝远(1986、1988、1990、1994)对西周青铜器铭文所作的一系列考察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证据支持,从铭文中可知周王确实为最高土地所有者,诸侯在周王之下只拥有部分权利,李朝远称之为“领主制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杨师群(1993、1997、1998、1999、2000、2003a、2003b)则研究了中国古代各时期的产权史料,并以西方古代社会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认为我国古代存在财产私有的事实,却无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在民间社会经济运作的小秩序中,我们似乎模糊感觉到自耕农土地私有权的存在,而在国家专制统治的大格局中,实际上自耕农往往并无土地私有权可言;就是说自耕农的产权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服从国家大格局的运作规则,这时自耕农就被剥夺了排他的任意处置权”(杨师群,2003a)。
近年来随着产权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传统社会产权性质的探讨也开始摆脱数十年来所有制思维的羁绊,不再强调“公”、“私”之争(李根蟠,2014),而是转向对经验材料的深入挖掘,出现了大量考察产权形态实际运作的文献,这是传统社会产权研究的第三个时期。
其中江太新(1990、2000)较早地利用清代各地方契约和税收底册材料对传统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至少就清代前期的史料来看,宗法关系对地权约束不强、土地买卖频繁。赵冈(2002)亦利用统计资料来佐证自己有关中国古代土地私有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不存在大地主经济,地权往往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趋向于分散,所谓“地主”是私有产权下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胡英泽(2008、2011)则以“鱼鳞册”为材料来重新考察“关中模式”,认为秦晖所言关中地区土地地权分散、流转缓慢的结论是由于资料使用不当所致。
耿元骊(2008、2010)、陈明、刘祖云(2014)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梳理肯定了杨师群的观点,即我国古代无明确的产权制度,文献中的产权现象实则为赋税制度,“赋税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资源,土地之于传统国家统治的实际功用首先体现为其上的产出和税赋,这就导致了土地制度往往是作为租税制度的副产品出现的”(陈明和刘祖云,2014)。
上个世纪80年代,杨国桢利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并结合现代法权理论,开创性地研究了永佃权和“一田两主”等地权问题(杨国桢,2009)。①。此后,李锡厚(1999)、曹树基等(2010)、龙登高(2009)、戴建国(2011)、杜恂诚(2011)、春杨(2011)、曹树基(2012)以及龙登高等(2013)这些文献也皆以现代法权理论作为参照系,试图解释传统中国产权之特征。例如李锡厚(1999)、戴建国(2011)和春杨(2011)的研究引入现代法权理论的相关概念来分析宋代田宅典卖、明清田土找价回赎等问题;曹树基等(2010)将传统社会产权界定为“残缺产权”,即是以现代意义的刚性产权制度作为参照系而形成的比照;而杜恂诚(2011)认为上海租界地区的“道契”制度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产权;龙登高等(2013)则使用现代产权概念将明清时期的田土买卖分解为一套包含“胎借-租佃-押租-典-抵当-活卖-绝卖”等多样化形式在内的地权交易体系,并结合土地交易史料认为当时的地权交易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基于身份关系的交易”(personal exchange,龙登高,2009) 龙登高(2009)②。不过与国内学者侧重于探求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契合性研究不同,国外学者如曾小萍(2011)、埃里克森(2012)等人则注意到了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背离之处,譬如曾小萍认为清代政府确实承认私人产权,但这类私产不同于西方概念,其权利属于家庭而非个人(曾小萍, 2011, 第21页)。
① 同样,本文参考的是杨国桢于2009年出版的修订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② 一文中将personal exchange翻译为“人格化交易”,这实际上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一种错误理解。因为“人格化”的汉语本意是童话语言创作惯常使用的一种方式,赋予动植物等非人生物以人的特征,例如小动物会说人话等,与该词英语本意相差甚远。
林济(2001、2003)代表了另一种研究趋势,通过对中国近代乡村财产习俗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种“财产祖有”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家族公产还是家庭私产,其本质上都是“祖先私有”(林济,2001)。①与此观点相似,桂华、林辉煌(2012), 陈锋(2012、2014)、谢小芹、简小鹰(2014)以及徐嘉鸿(2014)等“华中乡土派”学者纷纷使用“祖业观”、“祖业权”等概念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产权观念对当代的影响。②因为他们认为西方产权理论(以经济学为代表)不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经验;从中国经验中所反映出的产权观念仍然在左右着当代中国农村地区的产权实践,抵触着现代产权规则的施行,这种影响不容忽视。
① 林济这一观点,应当与科大卫、刘志伟(2000)对于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密切相关,因为财产祖有的观念源自传统地方社会祖先崇拜的社会信念(social belief)。受本文主题和篇幅所限,对该理论的逻辑展开笔者将另具文探讨。
② 笔者所见“华中乡土派”这一称谓,是来自谢小芹、简小鹰(2014),但这一名称应该有更早的出处,笔者未及考证。“华中乡土派”主要是以贺雪峰为代表的、来自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CCRS)的农村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与政治学者。并且谢小芹、简小鹰(2014)一文认为“祖业观”是该学派原创性观点,这其实是忽视了华南研究学者早期的贡献。
三、 反思“我曾经想过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一个中国传统家庭的财产归谁所有?在没有分家之前,或没有遗产继承之前,所有子女似乎都享有部分收益权,但都没有处置权,这是很明显的。但能说父家长拥有所有权吗?从道理上说,他只是代表全家拥有它,必须从全家的整体利益去支配它。似乎只能说是‘家庭所有’。一个只管自己消费而不顾一家老小的家长,从情理上,我们不会认可为他是合格的家长。但这样的家长,在中国历史上可惜不少。再说,子女没有所有权,那凭什么分家时他必须取得其中的一份财产呢?其中不是隐含了一个早已预伏的前提:全家的财产里,他也有一份,只是必须按大家认定的习惯法则,由家长来决定时机和份额”(王家范,1999b)。
王家范先生的这段论述反映出我们在分析有关传统社会的产权材料时所面临的一种普遍困难:古代中国的产权现象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事态,冠之以任何当代的产权理论似乎都有一叶障目之嫌。接下来笔者将以清代闽北地区的土地买卖文书为例,反思上一节所提及的产权理论,以厘清本文的产权分析思路。
笔者选用的资料出自杨国桢(1982a、1982b、1982c)分三期刊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本文只取用了其中土地买卖文书部分,共81件。③
③ 这批文书档案中还有一批土地租佃文书,本文没有讨论。
之所以采用闽北土地文书作为本文的材料,理由有四:一是这批文书是杨国桢先生于1979年从三千多件契约文书中辑选而来,所涉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二是闽北山区在历史上其经济地理位置具有参考价值,一方面作为福建地区的“粮仓”,传统农业经济发达,另一方面明清以来又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影响,因此该地区的田土买卖更能凸显出传统中国社会财产权利的某些典型特征;三是这批资料时间跨度长,从1654年(顺治十一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二百多年时间,基本上能代表整个清代时期该地区地权关系的态势;最后,该文书材料相当成熟,除了杨国桢外,其他学者也多次采用,例如江太新(1990),其中疑议甚少,所以若能从中发现某些新的线索,则更具有说服力。
通过考察这批文书资料,本文认为前述学者观点中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是早期学界产权讨论中的“公”-“私”之辨。笔者认为从“公有”、“私有”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的财产权利本质上仍然是基于西方经验传统。因为所谓public (公)与private (私)的划分源自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当一位自由民作为“公民”参与城邦事务时,其处理的是“公”领域的关系;当他作为“家父”进行家政管理时,处理的则是“私”领域的关系。而当家庭财产成为决定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基础之后,财产私有的观念才逐步成熟,并相应地激励了保障财产权利的法律规则的完善。①但是反观中国,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商周时期并未产生“私”之观念,因为在甲骨文、金文中没有“私”字(杨师群,2003)。而对应的“公”字古义为贵族之爵号,即“公侯”之意。《诗经·小雅·大田》中所言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及先秦文献中“公作”与“私作”之辨,②皆反映出一点: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公”代表着国家、社会所肯定的正式规则、秩序,而“私”是在官方律法之外的非正式约束、潜规则。③延伸开去,在汉唐契约中我们经常见到类似“官有政,民私要”这样的语句,④正反映出传统社会对“私有”属性的一种普遍认知。汉唐之后,随着官府开始逐步承认私契、将私契作为诉讼证据并对私契课税,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语句,但是从闽北契约中我们仍然能见到“系两家甘允,各无异说”(康熙年间第4件、乾隆年间第1件等)这样的用语,表明此时田土的买卖仍旧维系于一种私约性质(杨国桢, 2009, 第18页)。当财产权利依赖于正式规则缺失下的非正式约束而存在时,“公有”、“私有”这样的划分就失去了意义。
① 所以著名的罗马“十二铜表法”中五表为“私法”(民法),“公法”(刑法)只有二表。
② 譬如,“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商君书·垦令》)。
③ 所谓“公田”即公侯贵族之田产,这是得到国家权力承认的,在此田土上的劳作为“公作”,因此“公田”绝不是“公有产权”,而是贵族获得国家授权的财产。在“公作”之余,开垦“公田”之外的田土,即为“私作”,所以“私田”也不是“私有产权”,而是在国家正式授权的田土之外私自耕作的“民有”土地。
④ 例如吐鲁番文书中就常见有这种表述,尽管具体行文或稍有差异,参见韩森(2008,第25页)。
其次,是西方产权理论的移植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直接运用源自西欧历史经验的产权概念来解析传统中国社会的产权资料呢?例如中国特有的地权交易形态,“典”--有赎回权的土地转让,⑤戴建国(2011)将其纳入现代物权理论的解释,认为出典人出让的是使用权;而龙登高等(2013)则认为典是他物权的交易,并且进一步细化,将典与胎借、租佃、押租、活卖、绝卖等作了区分,“地租交易谓之胎借,土地使用权交易谓之租佃,他物权交易谓之典,押租介乎佃、典之间,担保物权交易谓之抵押,所有权交易谓之买卖”,从而建构起一套多样化的地权交易体系,并认为这套交易系统在清代地权市场已经成熟。①
⑤ 关于“典”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黄宗智(2007,第61页)、孔迈隆(2011,第46页)等学者的表述基本接近,学界对此也已形成一定的共识(曹树基,2012)。
① 换言之,龙登高等人的观点认为,在清代传统经济内部,已经孕育出现代化市场交易形态。
倘若现代产权规则能够适用于分析传统社会的产权经验,那么即便不存在成文法的明文规定,我们也应当能够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史料予以佐证。但是在闽北土地买卖文书中,两个十分特殊、却又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引起笔者注意。
第一个案例是一块名为“大新源”的田土买卖。该土地交易在闽北文书中最早见于乾隆十二年,由罗恭智将此“祖产”卖于赵天若,②并约定十年之内原价赎退,若过十年之外,不得赎回(乾隆年间第5件)。按照前述理论,这是标准的典。不过仅三年之后,罗恭智便与赵天若立找贴契,要求找价银十二两,并且特别注明,“所找所贴,二比情愿,自找之后,听凭买主永远管业,卖主向后不得取赎,以及登门索找讨贴,任凭买主过割收产入户,卖主不得阻当异说”(乾隆年间第7件)。③据龙登高等学者的观点,这属于一次性找断交易,当为“绝卖”,所有权在此时发生了转移,后续也不应再有回赎、找价等行为。然而,乾隆二十五年,罗恭智以同一田土再立找贴断契,此时买主已不是赵天若,而是赵宜珪,从文书内容和姓氏上看应为赵天若后人。也就是说,即便原买主过世,该土地产权仍未彻底交割,原卖主仍可向在世后人找价。此外,该契约依然注明为找断契,卖主不得再找(乾隆年间第14件)。④可是七年之后,罗恭智又一次向赵宜珪重找,尽管所立文书还是写明找断贴契,不得再找(乾隆年间第17件)。乾隆三十六年,名为罗启玉、罗启亮二人,就土名“大先源”的田地向赵宜珪找价。尽管名称有所出入,但从文书内容来看,这块“大先源”即为“大新源”之笔误,罗启玉、罗启亮之先父即为罗恭智。也就是说,在原买卖双方均已过世的情况下,罗氏家族仍有权向赵氏家族招贴,此外文书中强调这是“休心断骨契”,永不再找(乾隆年间第20件)。之后从乾隆三十七年的一份找贴契中可知,该田土在同年(三十六年)被赵宜珪卖于刘子龙,⑤并在一年后向刘子龙找价一次,当然契中依然声明是“找断”,不得再找(乾隆年间第22件)。意料之中的是,两年之后,乾隆三十九年赵宜珪又与刘子龙立找断契(乾隆年间第24件)。由此,这块“大新源”的土地在二十七年时间里转手两次,找贴至少七次(其中一次招贴契未收入,但有记载)。
② 要注意的是,在这份最早的买卖文书中并未特别说明是祖产,而是在十三年后的找价契中才注明“承祖遗下有粮田一号”(乾隆年间第14件)。
③ “找贴”、“找价”,含义相同,即土地卖售、银货两讫之后,卖主又再度要求买主支付额外的溢价银。各地文书中称呼略有不同,但这类现象在经济繁荣期、地价波动时很常见。一次性的找价又称为“找断”,即以后不再找贴。
④ 该文书内容还透露出,在乾隆十八年罗恭智就已经再次找贴(前次是乾隆十五年)。
⑤ 因为缺少赵宜珪与刘子龙的买卖契,笔者不能确定罗氏后人的找价契是在赵宜珪卖地之前还是之后订立的(土地转手后再被前卖主索要加价的行为在当时亦屡见不鲜)。
第二个案例发生于乾隆五十六年,一块名为“水角壠”的土地买卖。卖者为刘应菁和其侄子刘兆荣,该田土注明为刘应菁兄之遗产,田皮田骨一并卖于林长标。此处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该土地买卖文书间隔一月立契两次,分别为乾隆年间第34、35件,其差异之处除了地价银有少许差别外,主要就是前一件文书中写明是“卖断契”,后一件只写“卖契”,由此该土地交易应属于“活卖”性质。所以一月后,刘应菁、刘兆荣再与林长标立找断契,且找价甚高,原卖地价为纹银62两,找价却要34两。也就是说该田地在一月内涨价超过50%(乾隆年间第36件)。两、三年后,林长标将“水角壠”卖于刘子飞,并于三月之后向刘氏找贴,立找贴断契(乾隆年间第38件)。①但是两年之后,刘应菁再次向林长标立贴断契(嘉庆年间第1件)。②注意此时林氏已经将田地转手,但契约仍然成立。不过紧接着就是林长标向刘子飞立找断契(嘉庆年间第2件)。一月后,刘汉宝为“水角壠”地块向其族侄刘应菁立找杜断契(嘉庆年间第3件),该文书中写明这块土地最早其实是从刘叔汉宝处买得,但尽管数次转手,最初所有者的田土权利仍未割断。十二年后,一位名为林胜德的人向刘子飞就“水角壠”这块田地再立找贴断契(嘉庆年间第9件)。从文书内容可知,此人为林长标之子,且契中写明该田地之前就已“经找数次”,但和前例相似,后人依然有权不断找价,并且三年之后又一次立找贴断契(嘉庆年间第11件)。
① 笔者未见卖地契,只见找贴断契。找契中书“本年十月”卖地,但该契却是立于乾隆六十年一月。所以这里应有误,要么是“十一月”误作“一月”,要么不是“本年”而是前一年卖地。
② 该文书中断契字人名为“刘应青”,从内容来看,应为“刘应菁”之误。
从上述两个特征性案例中就可以发现,前文所述的那些法权理论在面对这些经验材料时几乎完全无用。像“胎借、租佃、押租”这些问题因为涉及到我们没有讨论的租佃文书,暂且不论。至少就“典、活卖、绝卖”这些地权交易形式来说在闽北土地买卖文书中根本难以分辨:注明绝卖,仍可找价;注明找断,仍可一找再找,所谓“不得再找”这些用语,形同虚设;且无论经多少人手,土地权利仍依稀维系于最初权利人--无论在世与否,连绵不断、难以割绝。所有这些现象,毫无现代法治规则可循,使用现代产权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得出结论说,不存在一般化的理论,只存在特殊经验,认识中国社会的产权,只能从中国经验出发得到所谓中国式理论呢?这正是本文要反思的第三个问题。如果以中国经验特殊论的观点来分析闽北文书,那么我们得不到任何可确定的认知,只有一堆模棱两可的材料堆积。③比如从这些文书中可以发现,是否在契约中附上“回赎”条款,并不够成“典”与“卖”的区别;曹树基等(2010)从石仓契约中发现的“标明回赎时间的卖田契,都不存在找价的问题”这一经验规律在此也不适用;④而黄宗智(2007,第63页)、春杨(2011)所讨论过的“找贴”时限问题,亦不确定,乾隆年间第21件文书表明,一块田土在崇祯年间出卖,康熙六十一年招贴一次,乾隆三十七年再次找断,远远超出清代律法30年时限的规定;⑤还有关于“回赎”的期限,黄宗智(2007,第67页)看到宝坻案件材料中最长可达77年,但是在闽北文书中一块名为“冷岩仔”的土地,康熙年间出卖,嘉庆十六年赎回,远远超过了77年的时限。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说我们希望从中国经验中发现特殊的理论,那么这种特殊理论又为何物?黄宗智说这是“前商业逻辑”(2007,第67页),华中乡土派的学者说这是“乡土社会”的传统(桂华、林辉煌,2012)。但是从闽北文书材料所反映出的经验现象中,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恰恰是一种类似龙登高等学者所言的、有悖于传统的现代市场化交易逻辑--土地交易明显地显示出一种“趋利”特征:越是经济发展迅速时期(例如乾隆年间),土地流转愈频繁、地价波动愈剧烈、找价情况愈演愈烈。完全有悖于安土重迁的“前商业”逻辑和“乡土社会”传统。所以说仅仅依靠经验,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传统中国财产权利的本质。
③ 当然,反驳者也可以说,这是由于笔者的分析样本过小所致。不过我相信如果坚持当年德国历史学派所倡导的经验特殊论来处理材料,随着样本的扩大,这种不确定性的境况只会是变得更加严重。
④ 即第一个案例中乾隆年间第5、7件文书所反映的情况。
⑤ 所谓“30年时限”,由乾隆十八年例所定,“嗣后民间置卖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未明,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无绝卖字样者,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卖论,概不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当然,春杨(2011)也承认30年期限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执行,他解释为是“地方官员在执法中灵活变通”。
① 文书中未说明是康熙何年卖地(原卖契丢失),但即便是从康熙六十一年开始起算,到嘉庆十六年也长达89年。且这块土地发生过争讼,乾隆年间第21件文书中所涉即这块田土,文书内容明确指出在康熙六十一年有关这块田土的招贴(最初买卖是崇祯年间)官府作出过判决,认为招贴有效。
四、 中国特色的产权:宗法财产权本文一以贯之的观点是:要认识传统社会财产权利的性质,就必须从具有特殊性的经验材料中找到蕴涵于其中的一般性事实。那么从闽北文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何种一般性事实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
一是宗族在传统社会财产权利实践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在乡族共同体内部,个人的活动和对其土地和财产的支配是存在的,亦即有私人土地所有权,但私人的土地权利受到乡族共同体的限制和支配”(杨国桢, 2009, 第4页)。几乎所有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财产权利的行使或多或少都夹杂着某种“宗族”(lineage)关系。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宗族关系对财产权利的约束已趋松弛(江太新,1990),甚至突破了“基于身份关系的交易”(龙登高,2009)。
② 本文对于“宗族”一词的理解,采取的是钱杭(2009)的观点。将“宗族”对译为“lineage”,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2000)中就已使用,并成为国际学界一种通行做法。但是国内到目前为止依然有很多学者将“宗族”对译为“patriarchal clan”或“patriarchy”,这实际上反映出对“宗族”性质的不同理解。
那么闽北文书中所见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当年江太新先生在运用闽北文书时以土地买卖双方是否是同姓(亲房)作为标准,判断宗族在土地交易中的约束力。共统计文书77件,计得异姓间交易61件,占79.2%,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土地交易突破了宗族桎梏,趋向于自由买卖(江太新,1990)。
笔者认为这样的统计过于草率。而且以此推论,如果土地交易大多在异姓间进行,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同姓聚居村落必然会转变为异姓混居村落。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就如江太新(1990)中所见,像徽州这类土地交易极为频繁的地区,宗法关系似乎也是时强时弱,并未打破同姓聚居的局面。
如果以现代产权规则下的交易作为参照系,来比照传统社会,那么本文认为土地买卖文书中出现以下5类情形中任何一种,皆为“受限产权”:①(1)附带回赎条件(明文约定或实际有赎退情形);(2)找贴、找断契;(3)亲族间买卖(包括同姓和异姓);(4)契中写明亲房优先但不受;②(5)附带“亲房不相干涉”条款。其中(1)、(2)条表面看来与宗族无关,但是这类中国特有的土地转让规则能够得以执行的现实基础正是来自于宗族组织所规定的身份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财产祖有、荫庇后世的权利观念;③而(4)、(5)条江太新认为只是格式条款无实际意义。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是纯粹现代意义的私有产权,那么这些限制个人财产处分自由的格式条款根本就不会存在,其存在形式本身就是宗法关系影响的体现。
① 此处所言“现代产权规则下的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依照现代法律规定某物归属于某人所有,权利人即可合法地处分财物。倘若处分权受限,且受限原因不是由于法律规定之特殊、例外等情形,那么即可认为是前现代意义上的“受限产权”。
② 即先询问亲房是否购买,无人愿受之后再卖于异姓。
③ 在不少契约文书中都明确写道,支持卖主“回赎”、“找贴”诉求的,并非官府律法或是非法强制,而是“亲房言谕”、“亲友劝谕”。这显示出当时的宗族组织在土地交易中实际上发挥着非正式约束的作用。
所以按照上述5类条件,笔者对闽北文书81件契约重新进行梳理,结果如表 1所示:
| 表 1 清代闽北地区土地买卖情况 |
由于有些契约文书中具有上述5类情形中的2类以上,所以受限产权契约的统计有重复计算。但是无任何约束的田土自由买卖--即可视为符合现代产权规则的土地交易契约,仅有6件,占7.4%。其余75件契约中所见的土地买卖,地权均受约束。这就足以说明宗族组织的重要性,它实际上是财产权利是否能够得以实践的客观基础。
第二个一般性事实是“财产祖有”的观念。在闽北文书中,“承父遗下”、“承祖遗下”、“父手遗下”这类用语极为常见。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用语并非普通的修辞,而是表达出当时人们对于“为何一块田土归我所有”、“为何我有权处分特定田土”、“为何我能够对已卖出土地索取权利”等等产权事态的主观认知,即“财产祖有”的观念。如上节所述的第一个案例,卖主罗恭智最初并未提及他是如何获得“大新源”这块田土的处分权的,但是在经过数次找价且原买主已过世的情况下,十三年后的招贴契中明确指出这是“祖产”。换言之,在罗恭智的理解中正是“财产祖有”的观念赋予其充分、正当的理由能够向买主后人再度找价。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何传统社会中土地交易会出现那种权利转移藕断丝连、难以割舍的现象;才能够厘清土地最初权利人及其后代所拥有的那种跨越时间、无限追索权的合法性基础究竟是什么;才能够明白“典、活卖、绝卖”这些交易形式为何在当时的实践中总是混同在一起,以至于不能使用现代产权规则将其条分缕析。①因为“土地的最后绝卖,特别是世代相传的土地的绝卖,虽然不是绝对禁止的,但被认为很少可能。这种土地,在理论上的确没有被认为完全是占有者或所有者的个人财产,而一般都认为它是占有者的家庭或宗族的遗产”(林济,2001)。
① 其实“一田两主”的现象更能说明这种“财产祖有”观念在传统社会产权实践中的影响,但是限于篇幅,本文未作讨论。
笔者曾指出,作为切实有效的制度事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方钦,2016):(1)可观察到的行为之常规性(a regularity of behavior);(2)遵循行为常规性之行动(following the regularity of behavior);(3)遵循行为常规性之意向(the intention to follow the regularity of behavior)。
现在,从闽北土地买卖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一般性事实,我们可以(1)观察到当时人们在私约关系下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田地的通常行为模式(行为的常规性);②(2)通常情形下皆以宗族组织为基础施行这类产权行为;(3)当行为人采取此类行动时,他们对交易行为本身及其标的物(田土)的主观认知持有一种“财产祖有”的观念。
② 尽管这类行为模式以现代产权理论看来相当混乱、“残缺”。
综上所论,本文将传统中国社会的财产权利定性为“宗法财产权”(Lineage Property Rights)。
在此补充几点说明。首先,从笔者使用的英语名称就可以发现,准确的称谓应当是“宗族产权”。但是由于汉语语境中“宗族产权”有一种“集体产权”的意思,出于上一节对“公”、“私”之辨的分析,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笔者采用了“宗法财产权”这一对译。
其次,特别要强调的是“宗法财产权”之“宗族”指的是“世系”而非“血缘”意义上的组织(钱杭,2009),亦即“宗法”原初之意,“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礼记·丧服小记》)。③也就是说,笔者认为传统社会的宗族最重要的特性就是一个按身份等级秩序为原则进行世系建构的组织,早已突破了那种原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式。
③ 亦可见,“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礼记·大传》)。二者意思相近。
由此可以推出最后一点,即“宗法财产权”的核心是要说明传统社会的财产权利是一种以身份关系作为基础的资源安排:并非是个人的财产决定了其在社会秩序中的身份,而是其身份决定了个人对于财物的可控制能力。这是东西方产权制度最为关键的区别。这也就能够解释第三节开头王家范先生所思虑的问题,作为宗族组织中的一员,个人的财产权利取决于他的身份。“一家之长”对于财物的处置权利肯定高于子女,但更大的“家长”,一族之长亦能干涉族内成员的财产权利,进而上升到国家层面,皇帝是最高的“家长”,因此皇权当然能够干涉个人产权。不过倘若按此等级秩序回溯,我们可以发现世系的尽头就是“祖先”,所以理论上而言祖先才是最终的权利人,拥有完整意义的财产权利,所有在世者不过是作为祖先的代理人在行使着财产权利。
五、 余论本文是一次初步尝试,目的是希望从经验材料的梳理分析中,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产权制度作出定性分析。
正如本文之前所指出的,目前学界对传统社会产权资料的处理存在两大误区:一是不加区别地套用现代产权理论来解构传统社会的产权形态,这样的做法不仅曲解了前现代世界的产权现象,而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量分析也难以让人信服;二是盲目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并希望从中提取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理论”,这种曾经为德国历史学派所倡导的研究进路危害更为严重,因为其不仅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而且固步自封,似乎只有从“乡土社会”中内生出来的社会制度才是合理的,这对于正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此类理论主张只能是一种观念上的阻碍而非进步。
当然,本文的分析并没有完结,至少还遗留下两大问题,笔者将另具文探讨。在此暂且先将这两个问题提出。
第一个问题是在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中“宗法财产权”会产生何种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这种传统社会的产权制度在当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影响。正如华中乡土派的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所见到的,“尽管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和支配实际形态随着制度变革而变化,而他们骨子里关于土地产权的认知却保持了稳定性”,“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祖坟山、祠堂及所在土地、林地、荒山、老宅基地、责任田都共同反映出农民对于‘祖业’的认知,而祖业观虽然与国家界定的产权观念相冲突,却构成了一种‘地方性共识’,影响着国家的法律实践”(陈锋,2012)。因此,深入分析“宗法财产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特征性事实至关重要。在此,笔者只是简单地指出,“宗法财产权”由于其最终权利人是“祖先”,而在世族人只是代为行使财产权利,这就类似于一种“委托人缺位的代理制度”。从这一角度出发,以德·索托所言的产权效应作为参照系,我们可以发现东西方产权制度实质上的差异,并能认识到那些看似混乱的传统社会产权现象背后其实存在着一套清晰的统一逻辑。
第二个问题是“宗法财产权”中三个要素--财产权利、宗族和祖先观念--相互之间如何发生影响?首先要指出的是“祖先崇拜”的观念其实是传统儒家观念的内核。①科大卫、刘志伟(2000)对于华南宗族意识形态基础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回答该问题的线索。简言之,在传统社会中,财产权利的行使以宗族组织为基础,宗族组织的维系依赖于儒家观念,儒家观念的维持又需要行使财产权利所提供的经济基础;反过来,财产权利的施行增强了宗族组织控制资源的能力,宗族组织为了维系自身又进一步培育和巩固传统观念,而这类传统观念意识又为财产权利的合法性提供人情伦理的支持。由此,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构成了一个自我施行(self-enforcing)的产权制度复合体。
① 注意,这里所指的是“儒家观念”,而非士人阶层所持有的“儒家思想”。关于“观念”的“思想”的区别,笔者采纳的是金观涛、刘青峰(2009,第3页)对于“观念”的界定。
| [] | 《春秋左传正义》,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1980年版. |
| [] | 《礼记正义》,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1980年版. |
| [] | 《毛诗正义》,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1980年版. |
| [] | 《孟子注疏》,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1980年版. |
| [] | 《商君书锥指》, 《新编诸子集成》, 中华书局1986年版. |
| [] | 《慎子》, 《诸子集成》, 世界书局1935年版. |
| [] | 班固, 《汉书》, 中华书局1962年版. |
| [] | 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2008年版. |
| [] |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http://www.oalib.com/references/15739254 |
| [] |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银雀山汉墓竹简》(一), 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http://www.doc88.com/p-2116615154127.html |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 [] | 曹树基 , 2012, "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变动的一般理论", 《学术月刊》 , 第 12 期 , 第 117–125 页。 |
| [] | 曹树基、 李楠、 龚启圣 , 2010, "'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1728-1949)", 《历史研究》 , 第 3 期 , 第 118–131 页。 |
| [] | 陈锋 , 2012, "'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基于对赣西北宗族性村落的田野考察",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第 2 期 , 第 68–76 页。 |
| [] | 陈锋 , 2014, "从'祖业观'到'物权观':土地观念的演变与冲突--基于广东省Y村地权之争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 第 6 期 , 第 25–36 页。 |
| [] | 陈明、 刘祖云 , 2014, "传统国家治理逻辑下的地权运作", 《中国农史》 , 第 3 期 , 第 86–95 页。 |
| [] | 程念祺 , 1997, "试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公有、私有与国有问题", 《史林》 , 第 3 期 , 第 1–9 页。 |
| [] | 程念祺 , 1998, "论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基础的不稳定性", 《史林》 , 第 2 期 , 第 21–29 页。 |
| [] | 程念祺 , 2000, "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 《浙江社会科学》 , 第 4 期 , 第 105–110 页。 |
| [] | 春杨 , 2011, "明清时期田土买卖中的找价回赎纠纷及其解决", 《法学研究》 , 第 3 期 , 第 175–193 页。 |
| [] | 戴建国 , 2011, "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 《历史研究》 , 第 6 期 , 第 99–117 页。 |
| [] | 杜恂诚 , 2011, "道契制度: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 《中国经济史研究》 , 第 1 期 , 第 3–11 页。 |
| [] | 方钦 , 2016, "制度:一种基于社会科学分析框架的表诠", 《学术月刊》 , 第 2 期 , 第 66–75 页。 |
| [] | 高敏, 1960, "我国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吗?", 《光明日报》, 3月31日. |
| [] | 耿元骊 , 2008, "'土地兼并'与唐宋间地权的流变",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4 期 , 第 78–82 页。 |
| [] | 耿元骊 , 2010, "'土地还授'与唐代'均田制'研究--制度得以成立的实施机制", 《江汉论坛》 , 第 6 期 , 第 79–83 页。 |
| [] | 桂华、 林辉煌 , 2012, "土地祖业观与乡土社会的产权基础", 《二十一世纪》 , 第 2 期 , 第 108–117 页。 |
| [] | 韩国磐 , 1959, "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 《历史研究》 , 第 5 期 , 第 29–64 页。 |
| [] | 韩森, 2008,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http://www.bookask.com/book/1843352.html |
| [] | 侯绍庄, 1957, "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的自耕农与国家佃农的区别--和胡如雷先生商榷", 《光明日报》, 1月3日. |
| [] | 侯外庐 , 1954,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 《历史研究》 , 第 1 期 , 第 17–32 页。 |
| [] | 胡如雷, 1979,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三联书店. |
| [] | 黄宗智 , 2005a,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 第 1 期 , 第 83–93 页。 |
| [] | 黄宗智 , 2005b, "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 《读书》 , 第 2 期 , 第 3–14 页。 |
| [] | 黄宗智, 2007,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上海书店出版社. |
| [] | 胡英泽 , 2008, "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 《近代史研究》 , 第 3 期 , 第 117–139 页。 |
| [] | 胡英泽 , 2011, "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 《近代史研究》 , 第 4 期 , 第 134–148 页。 |
| [] | 江太新 , 1990, "略论清代前期土地买卖中宗法关系的松弛及其社会意义", 《中国经济史研究》 , 第 3 期 , 第 72–83 页。 |
| [] | 江太新 , 2000, "论清代前期土地买卖的周期", 《中国经济史研究》 , 第 4 期 , 第 25–33 页。 |
| [] | 金观涛、刘青峰, 2009,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法律出版社. |
| [] | 科大卫、 刘志伟 , 2000,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历史研究》 , 第 3 期 , 第 3–14 页。 |
| [] | 孔迈隆, 2011, 《晚清帝国契约的构建之路--以台湾地区弥浓契约文件为例》, 载曾小萍、欧中坦和加德拉编, 《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35-84页. |
| [] | 李朝远 , 1986, "西周诸侯土地所有制的初步考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第 2 期 , 第 61–67 页。 |
| [] | 李朝远 , 1988, "论西周天子土地所有权的实现", 《江西社会科学》 , 第 3 期 , 第 117–121 页。 |
| [] | 李朝远 , 1990, "论西周土地交换的程序", 《江西社会科学》 , 第 6 期 , 第 85–90 页。 |
| [] | 李朝远 , 1994, "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 《学术月刊》 , 第 11 期 , 第 59–64 页。 |
| [] | 李根蟠 , 2014, "官田民田并立公权私权叠压--简论秦汉以后封建土地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中国经济史研究》 , 第 2 期 , 第 3–11 页。 |
| [] | 李峰, 2010, 《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 | 李锡厚 , 1999, "宋代私有田宅的亲邻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第 1 期 , 第 46–54 页。 |
| [] | 林济 , 2001, "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述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第 1 期 , 第 56–68 页。 |
| [] | 林济 , 2003,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 《中国农史》 , 第 3 期 , 第 76–83 页。 |
| [] | 刘毓璜 , 1960, "试论西汉时代的小自耕农经济", 《江海学刊》 , 第 1 期 , 第 53–63 页。 |
| [] | 龙登高 , 2009, "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 《经济研究》 , 第 2 期 , 第 146–156 页。 |
| [] | 龙登高、 林展、 彭波 , 2013, "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 , 第 5 期 , 第 125–141 页。 |
| [] | 罗伯特·C.埃里克森 , 2012,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 《清华法学》 , 第 1 期 , 第 5–16 页。 |
| [] | 莫里斯·弗里德曼, 2000,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 启循 , 1979,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综述", 《历史教学》 , 第 6 期 , 第 36–37 页。 |
| [] | 钱杭 , 2009, "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 《历史研究》 , 第 4 期 , 第 50–67 页。 |
| [] | 秦晖、金雁, 2010,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语文出版社. |
| [] | 束世澂 , 1957, "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 《历史教学问题》 , 第 3 期 , 第 1–7 页。 |
| [] | 王家范 , 1999a, "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国有'性质辩证",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3 期 , 第 21–29 页。 |
| [] | 王家范 , 1999b, "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辨析", 《史林》 , 第 4 期 , 第 1–9 页。 |
| [] | 谢小芹、 简小鹰 , 2014, "'祖业权':作为一种非正式产权的地方表达与实践--基于对广西宗族性村落的调查",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1 期 , 第 56–62 页。 |
| [] | 徐嘉鸿 , 2014, "祖业亦或私产:论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对赣北z村征地纠纷的个案解读", 《广东社会科学》 , 第 3 期 , 第 198–207 页。 |
| [] | 杨国桢 , 1982a, "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第 1 期 , 第 111–121 页。 |
| [] | 杨国桢 , 1982b, "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二)",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第 2 期 , 第 102–116 页。 |
| [] | 杨国桢 , 1982c, "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辑(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第 3 期 , 第 99–106 页。 |
| [] | 杨国桢, 2009,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杨师群 , 1993, "春秋土地私有制问题的商榷", 《学术月刊》 , 第 3 期 , 第 41–47 页。 |
| [] | 杨师群 , 1997, "西周社会财产私有制问题的考察", 《学术月刊》 , 第 5 期 , 第 82–90 页。 |
| [] | 杨师群 , 1998, "论东周秦代社会财产私有权问题", 《学术月刊》 , 第 5 期 , 第 68–74 页。 |
| [] | 杨师群 , 1999, "汉唐间社会财产私有权问题考论", 《学术月刊》 , 第 8 期 , 第 85–92 页。 |
| [] | 杨师群 , 2000, "中世纪中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之比较", 《学术月刊》 , 第 9 期 , 第 67–74 页。 |
| [] | 杨师群 , 2003a, "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产权问题的考察--与西欧中世纪农民的比较研究", 《学术月刊》 , 第 8 期 , 第 66–73 页。 |
| [] | 杨师群 , 2003b, "中西方上古社会财产所有权法制建构的对立",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 第 6 期 , 第 73–80 页。 |
| [] | 张传玺 , 1978, "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三个阶段",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2 期 , 第 46–56 页。 |
| [] | 张越 , 2016, "'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 《中国史研究》 , 第 2 期 , 第 13–28 页。 |
| [] | 赵冈 , 2002, "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汉学研究》 , 第 1 期 , 第 441–452 页。 |
| [] | 赵冈、陈钟毅, 2006a, 《中国土地制度史》, 新星出版社. |
| [] | 赵冈、陈钟毅, 2006b,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新星出版社. |
| [] | 曾小萍, 2011, 《对战前中国产权的评论》, 载曾小萍、欧中坦和加德拉编, 《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17-34页. |
| [] | de Soto, Hernando, 2000, The Mystery of Capital, Bantam Press. |
| [] | Durlauf, Steven N., and Blume, Lawrence E., ed., 2008,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
| [] | Hume, David, 2007, A Treatise of Human Nar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