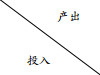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研发、设计、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若干个独立的环节, 并将每个环节配置于全球范围内能够以最低成本完成生产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那么具体到双边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应该如何核算两国的贸易收益?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中美两国既是政治大国,又是生产和贸易大国,据WTO统计,2013年,中美两国货物出口总额合计3.7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20.18%,中美双边贸易无疑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然而,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中,中美两国各自获取的贸易收益怎样呢?
一、 相关文献回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美两国分别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价值链环节,扮演无可替代的角色: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制造者,成为全球价值链加工组装等下游环节国家 (地区) 的主要代表;而美国是最大的最终产品消费者,成为全球价值链市场渠道等上游环节国家 (地区) 的主要代表。
“中国制造”和“美国消费”自然表现为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及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因而中美双边贸易背后的贸易收益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重点。国外学者如Samunelson (2004)运用传统的李嘉图自由贸易模型分析认为,在需求缺乏弹性的前提下,中国的技术创新将威胁美国的长期利益。Baily and Lawerence (2004)的研究认为,在2000-2003年间,美国制造业15%的就业机会减少要归因于自中国进口额的增加。Scott (2005、2008) 的研究也指出,由于中国劳动者低工资的竞争,1989-2003年美国失去了150万个工作机会,而2001-2007年的中美贸易逆差则造成约230万美国人失业。
国内学者宋玉华等 (2002)提出,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是一种补偿性逆差,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进口,满足了美国国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这种逆差不仅不会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反还有利于美国整体经济的运行。尹翔硕 (2001)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获得了大量外国资金,有利于调节美国的经济周期。在中美贸易中,双方都得益,逆差方 (美国) 的得益并不一定比顺差方 (中国) 小。刘光溪等 (2006)认为,中美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王苍峰等 (2009)认为,近些年来中美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此,中方得自贸易的相对利益不是增加反而是减小。
综合以上观点,国外学者大多从狭义贸易收益即出口对就业及增长等贡献的角度出发,由此判断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获得了更大的贸易收益。而国内学者则从广义贸易收益即进口对产业升级、消费者福利等贡献的角度出发,指出美国并非是中美双边贸易的受害者。因此,双方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很好揭示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本质。
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传统的出口核算方法存在大量重复计算,已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收益情况。针对传统贸易核算方法的缺陷,Hummels et al.(2001)从出口中分解出贸易增加值,以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收益。Koopman et al.(2014)、Daudin et al.(2012)、Lawrence.J.Lau (2007)等改进了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并进行实证应用,此后以贸易增加值研究贸易收益成为学术界主流。
基于增加值的贸易收益核算为厘清中美贸易收益提供了新的可行视角,曾铮等 (2008)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测算,发现中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刘建江等 (2011)通过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没有与贸易差额一致,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利微薄。
张咏华 (2013)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规模和中美贸易失衡程度进行了分年度、分技术类别测算,并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做了对比,发现传统的总量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中美贸易失衡程度。王岚等 (2014)利用增加值方法测度了16个货物贸易部门的中美双边贸易收益,发现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分工地位的差距导致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然而,正如Fung and Lau (1998、2003)、沈国兵 (2005)所认为,中美进出口贸易差额一定要考虑服务贸易因素。已有文献存在一个共同不足,即只是从制造业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差额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两国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差额情况。此外,贸易收益实现方式是反映各国获取贸易收益能力及特征的重要方面,以上文献并没有就中美双边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构建贸易增加值核算模型对中美双边出口额进行分解,进而从总体规模、行业结构、实现方式等层面对中美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双边贸易收益核算模型,对包括商品贸易及服务贸易在内的中美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更加细致的核算,从中反映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和定位,为改善我国对美贸易收益水平提供思路和方向。
二、 贸易收益的内涵及核算方法 (一) 贸易收益的内涵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链分割为若干个独立的模块, 每个模块都置于全球范围内能够以最低成本完成生产的国家和地区, 进而形成的多个国家参与产品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体系。这种分工模式下的贸易收益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获取的要素收益总和,如劳动者获取工资报酬、资本所有者获取资本回报、土地所有者获取土地收入等等,而收入法的增加值反映的正是各种要素的收入总和,因而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贸易收益可以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
另一方面,从统计核算角度来看,由于全球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不同分工国家之间频繁流入流出,一国出口中实现的不仅仅是本国要素收益,还包括他国要素收益,如中国、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出口加工型国家,其出口需求引致的资源品、中间品进口,实现的是进口国的要素收益。因此,贸易收益实际上就是出口中剔除中间品投入的剩余部分。
(二) 贸易收益的核算方法本文参考KPWW法及Neil Foster et al. (2011)的方法建立投入产出模型,其主要思路是通过分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一国生产对他国中间品投入的消耗,并把该部分从其出口中分解出来,剩余部分即为本国的贸易收益。
按照以上思路,首先假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出增加值率 (增加值/总产出) 为V;里昂惕夫逆矩阵为L=(I-A)-1(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明实现单位价值最终需求所需的总产出;国家间的贸易量用X表示。因而,L*X指为完成价值X的贸易量所需的总产出,而Tv=V′LX为完成价值t的贸易量所实现的增加值。
考虑到双边贸易情况,假设有2个国家 (国家1对国家2) 直接发生贸易关系,为简化运算,其他国家和地区 (ROW) 视为1个国家 (国家3),则产出增加值率向量为V′=(V1, V2, V3),其中V1, V2, V3分别表示参与贸易国的产出增加值率;贸易量向量为X=(X1*, X2*, X3*),其中X1*, X2*, X3*表示国家1、国家2和国家3之间的相互出口①。进一步将向量V′及X对角化进行矩阵运算,则:
①如X12、X13分别代表国家1对国家2和国家3的出口,X21、X23分别代表国家3对国家1和国家3的出口,X31、X32分别代表国家3对国家1和国家2的出口。
| ${\text{Tv = }}\left( {\begin{array}{*{20}{c}} {{{\text{V}}^{\text{1}}}}&{\text{0}}&{\text{0}} \\ {\text{0}}&{{{\text{V}}^{\text{2}}}}&{\text{0}} \\ {\text{0}}&{\text{0}}&{{{\text{V}}^{\text{3}}}} \end{array}} \right)\left( {\begin{array}{*{20}{c}} {{{\text{L}}^{{\text{11}}}}}&{{{\text{L}}^{{\text{12}}}}}&{{{\text{L}}^{{\text{13}}}}} \\ {{{\text{L}}^{{\text{21}}}}}&{{{\text{L}}^{{\text{22}}}}}&{{{\text{L}}^{{\text{23}}}}} \\ {{{\text{L}}^{{\text{31}}}}}&{{{\text{L}}^{{\text{32}}}}}&{{{\text{L}}^{{\text{33}}}}} \end{array}} \right)\left( {\begin{array}{*{20}{c}} {{{\text{X}}^{{\text{1*}}}}}&{\text{0}}&{\text{0}} \\ {\text{0}}&{{{\text{X}}^{{\text{2*}}}}}&{\text{0}} \\ {\text{0}}&{\text{0}}&{{{\text{X}}^{{\text{3*}}}}} \end{array}} \right)$ | (1) |
| ${\text{ = }}\left( {\begin{array}{*{20}{c}} {{{\text{V}}^{\text{1}}}{{\text{L}}^{{\text{11}}}}{{\text{X}}^{{\text{1*}}}}}&{{{\text{V}}^{\text{1}}}{{\text{L}}^{{\text{12}}}}{{\text{X}}^{{\text{2*}}}}}&{{{\text{V}}^{\text{1}}}{{\text{L}}^{{\text{13}}}}{{\text{X}}^{{\text{3*}}}}} \\ {{{\text{V}}^{\text{2}}}{{\text{L}}^{{\text{21}}}}{{\text{X}}^{{\text{1*}}}}}&{{{\text{V}}^{\text{2}}}{{\text{L}}^{{\text{22}}}}{{\text{X}}^{{\text{2*}}}}}&{{{\text{V}}^{\text{2}}}{{\text{L}}^{{\text{23}}}}{{\text{X}}^{{\text{3*}}}}} \\ {{{\text{V}}^{\text{3}}}{{\text{L}}^{{\text{31}}}}{{\text{X}}^{{\text{3*}}}}}&{{{\text{V}}^{\text{3}}}{{\text{L}}^{{\text{32}}}}{{\text{X}}^{{\text{2*}}}}}&{{{\text{V}}^{\text{3}}}{{\text{L}}^{{\text{33}}}}{{\text{X}}^{{\text{3*}}}}} \end{array}} \right)$ | (2) |
其中,等式 (1) 的第一个矩阵表示贸易参与国的产出增加值率,如V1、V2、V3分别代表国家1、国家2和国家3的产出增加值率;第二个矩阵反映贸易参与国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如L11代表国家1为实现单位价值最终需求,需要的本国总产出,L12代表国家2为实现单位价值最终需求,所引致的国家1总产出,以此类推;第三个矩阵反映贸易参与国之间的贸易流量。通过三个矩阵相乘,等式 (2) 的每一个向量都被赋予了经济含义。具体而言:
V1L11X12表示为完成国家1对国家2的出口额X12,所需价值L11X12的国内产出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部分 (Domestic value-added,DV)。
由于本国产品出口后可能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被进口国直接消费,从而直接实现国内增加值;二是进口国再次加工并出口到第三国,从而间接实现国内增加值;三是进口国再次加工并出口回出口国,该部分是通过本国进口而实现的,故被称为国内增值折返或复进口。因而,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 (DV) 又可以分为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 (direct value-added,dv)、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 (Indirect value-added,iv) 及国内增值折返②(re-import,ri) 三部分,即DV=dv+ iv+ ri。
②与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不同的是,国内增值折返是通过本国进口而实现的。
相应的在 (2) 式中,V1L12X23表示的是国家2对国家3价值X23的出口中,包含的属于国家1的增加值,该部分出口增加值是通过间接出口实现的,称为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 (iv)。V1L12X21表示的是国家1从国家2价值X21的进口中,实现的国内增值折返部分 (ri)。
因此,在国内增加值基础上,扣除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国内增值折返部分即为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部分 (dv),即被进口国直接消费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部分,故国家1对国家2出口实现的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部分dv=V1L11X12-V1L12X23-V1L12X21。
V2L21X12表示为完成国家1对国家2的双边出口额X12,所需国家2价值L21X12的中间投入中所包含的国家2的国内增加值,反映的是国家1出口实现的外国③增加值部分 (Foreign value-added,FV)。
③指国家1所需的中间品提供国。
三、 中美双边贸易收益的核算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①对中美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其中两国产出增加值率V、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两国贸易流量X数据②均来自国际投入产出表,涵盖的行业包括17个货物部门及18个服务部门。
①http://www.wiod.org/new_site/home.htm。
②由于WIOD数据库的国际投入产出表 (WIOT) 正是依据COMTRADE数据库而编制的 (Timmer.et.al, 2013) 本文以两国相互投入量 (包括中间品及最终品) 来衡量贸易流量, 与海关数据相比偏差并不明显,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2011年中国海关货物对美国出口额为3244.53亿美元,而按照WIOT的统计口径,中国对美货物出口额为3607.16亿美元,偏差率仅为10%,因而这种偏差并不影响两国贸易收益水平的度量。
| 表 1 国际投入产出表结构 |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对美国出口 (EXC,下标C代表中国,下同)、美国对中国出口 (EXA,下标A代表中国,下同) 进行增加值分解,剥离并汇总分别属于中国及美国的国内增加值。
(一) 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值分解从增加值的角度,中国对美的出口 (EXCA) 可以分解为中国出口增加值 (DVCCA)、美国出口增加值 (DVACA) 及其他国家出口增加值 (DVPCA)。
1. 贸易收益的总体规模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可核算出1995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包含的中国国内增加值及美国增加值。其中中国部门i对美出口包含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为ViCLiCCXiCA,其中ViC为中国部门i的产出增加值率;LiCC为中国部门i国内中间投入的里昂惕夫逆矩阵;XiCA为中国部门i的对美出口额。把各部门对美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加总,便可得出我国对美出口实现的国内贸易收益
为便于横向及纵向比较,构造贸易收益率指标DVR (贸易收益率表示单位价值出口创造的增加值份额,DVR=出口增加值/出口总额×100)。
如表 2所示,1995年以来,随着中国对美出口规模迅速膨胀,其包含的中国国内增加值及美国增加值规模亦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达4128.43亿美元,其中含大陆中国增加值2809.77亿美元,美国增加值36.85亿美元。从贸易收益率来看,中国对美出口实现的中国贸易收益率自1998年78.49%的高点后逐年下滑,2011年达到68.06%。中国对美出口实现的美国贸易收益率保持在1%左右波动,2011年为0.89%。
| 表 2 中国对美出口实现的贸易收益规模 |
按照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中国对美出口包含的中国国内增加值又可进一步分解为直接出口增加值 (dvCCA)、间接出口增加值 (ivCCA) 和国内增值折返 (riCCA) 三部分。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以2011年为例核算出中国国内贸易收益的行业分布及实现方式。
如表 3所示,首先,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电子及光学设备、纺织及制品、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等制造业部门,及以商务租赁为代表的部门。2011年中国对美出口实现国内增加值2809.77亿美元,其中电子及光学设备部门实现国内增加值949.12亿美元,占比高达33.78%。
| 表 3 中国对美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行业分布及实现方式 (2011年) 单位:亿美元 |
其次,由于两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差异①直接影响其贸易结构,进而影响贸易收益。从实现方式来看,中国对美出口实现国内增加值的主要方式为直接出口 (占比91.05%),即中国出口中间品及最终产品,并被美国就地消费;其次为间接出口 (占比7.96%),即中国为美国提供中间品,美国生产制造并间接出口到第三国;占比最小的为增值折返 (占比0.99%),即中国为美国提供中间品,美国生产制造并出口回中国。
①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黎峰.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收益——基于主要出口国家的行业数据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6):33-42.
以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为例,2011年中国该部门对美出口实现国内增加值949.12亿美元,其中直接出口方式实现879.60亿美元,占比92.68%;间接出口方式实现58.59亿美元,占比6.17%;而增值折返部分为10.93亿美元,占比1.15%。表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子及光学设备产品,绝大部分表现为最终产品并且被美国当地消费。
(二) 美国对华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按照以上思路,美国对华出口 (EXAC) 可以分解为美国出口增加值 (DVAAC)、中国出口增加值 (DVCAC) 及其他国家出口增加值 (DVPAC)。
1. 国内增加值规模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可核算出1995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包含的美国国内增加值 (DVA) 及中国增加值 (FVA),以及各自的贸易收益率水平。
如表 4所示,与中国对美出口实现的国内贸易收益相比,美国对华出口包含的本国增加值比例相对更高。以2011年为例,该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中,实现中方贸易收益占68.06%;而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中,实现美方贸易收益占81.8%。由此也表明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收益分配中居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国内增加值。
| 表 4 美国对华出口实现的贸易收益规模 |
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以2011年为例核算出美国国内增加值的各组成部分。
首先,从行业分布来看,美国对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电子及光学设备、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农林牧渔、化学原料及制品、金属压延及制品、交通运输设备等部门,此外,以公共管理及社会保障、商务租赁、航空运输为代表的服务部门也是美国实现国内增加值的重要来源。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实现国内增加值1434.21亿美元,其中电子及光学设备部门实现国内增加值302.44亿美元,占比高达21.09%。
其次,从实现方式来看,与中国对美出口类似,在美国对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中,大部分采用直接出口形式 (占比89.14%),其次分别为间接出口 (占比8.43%) 及增值折返 (占比2.43%)。然而区别在于,间接出口及增值折返两种形式占国内增加值的比重相对较高。仍以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为例,2011年美国该部门对华出口实现国内增加值302.44亿美元,其中直接出口方式实现219.78亿美元,仅占比72.67%;间接出口方式实现62.39亿美元,占比20.63%;而增值折返部分为20.27亿美元,占比6.7%。表明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电子及光学设备产品相当部分表现为中间品,并且通过对第三国出口及增值折返的形式实现。
| 表 5 美国对华出口的美国增加值行业部分及实现方式 (2011年) 单位:亿美元 |
在对中国对美出口、美国对华出口增加值分解基础上,可汇总出中美双边贸易的贸易收益情况。美国对华出口可以视为中国对美进口,由此核算出中美双边贸易的中方贸易差额。
如表 6所示,与增加值贸易差额比较,传统统计口径的中美贸易差额出现明显高估。2011年,按增加值统计口径,中方贸易顺差为1375.56亿美元,而按传统统计口径的中方贸易顺差为2375.03亿美元,高估程度为72.66%。
| 表 6 中美双边贸易收益汇总单位:亿美元、% |
分行业结构来看,根据表 7显示,与传统统计口径比较,增加值统计口径的贸易差额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其中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第二产业均出现了贸易逆差增加或贸易顺差减少,尤其是电子及光学设备部门,传统统计口径的贸易顺差为1418.66亿美元,而按照增加值统计口径,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822.47亿美元。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由于进口中间品包含有外国增加值,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贸易顺差被显著高估。
| 表 7 按部门划分的中美双边贸易收益汇总 (2011年) 单位:亿美元 |
另一方面,采用增加值统计口径后,第三产业出现了贸易逆差减少或贸易顺差增加,表明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能力逐渐增强。而服务出口的特征在于主要以中间品形式包含在货物商品中,而并非以直接出口为主,因而传统统计口径实际上低估了服务部门的出口能力。在中美双边贸易中,采用增加值统计口径后,除零售、水运、航空运输部门外,大部分服务部门均出现贸易逆差减少或贸易顺差增加,增加值贸易差额明显改善。
四、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出口并不能代表一国的贸易收益,贸易收益指出口中剔除中间品投入的国内增值部分。由于存在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问题,现行贸易核算体系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当前国际分工实际情况。
本文构建国际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贸易收益核算,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及启示:
1.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增加值核算方法是统计双边贸易收益的可行方法。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由于两国更多表现为垂直一体化的价值链分工,表现为大量的中间品在两国跨境流动,在贸易收益层面则表现为两国均包含着大量的对方国内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差额比较,传统统计口径的中美贸易差额出现明显高估。其中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贸易顺差被显著高估,而服务出口的贸易顺差被明显低估。这说明由于服务商品的特殊性,传统统计口径下的服务贸易收益大大被掩盖,且往往不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因而,我国应在国内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服务部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快适应国际规则融入国际分工,并大力发展对美服务贸易出口,从而提升我国对美贸易收益水平。
2.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对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电子及光学设备、纺织及制品、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等制造业部门,及以商务租赁为代表的部门。美国对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电子及光学设备、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农林牧渔、化学原料及制品、金属压延及制品、交通运输设备等制造部门,以及公共管理及社会保障、商务租赁、航空运输等服务部门。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绝大部分表现为最终产品并且被美国当地消费,而美国出口到中国很大部分表现为中间品,并且通过对增值折返及对第三国出口的形式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美两国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客观体现,在中美贸易分工中,美国更多处于研发、品牌、高端服务、关键零部件等价值链上游,主要为中国的生产制造环节提供中间品,由此决定了大量的美国国内增加值蕴含在“中国制造”之中,并通过中国的对外出口 (包括对美国出口) 而间接实现。相反,中国更多地处于加工组装等价值链下游,更多地生产并出口最终品,因而出口产品更多地被进口国当地消费,表现为直接出口的形式。
由此,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对美出口包含的本国国内增加值比重不到七成,而美国对华出口包含的本国国内增加值比重超过八成,表明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收益分配中居于相对有利的地位。预示着中美双边贸易收益分配与两国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密切相关,这也得到Koopman (2010)、黄先海 (2010)、于津平等 (2014)、孙天阳等 (2014)研究的支持。
因而对于中国而言,改善中美双边贸易收益的关键在于提升本国出口部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定位,尤其是电子及光学设备、纺织及制品等主要贸易收益来源部门而言,应改变扩大出口规模及市场份额的目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品牌开发及渠道拓展等领域的投入,培育和积累智力、品牌、营销渠道等高级生产要素,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价值,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定位,进而改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贸易收益。
| [] | Rifflart, , Daudin, C. and Schweisguth, D. , 2011, "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4(4), 1403–1437. DOI:10.1111/caje.2011.44.issue-4 |
| [] | Fung, K. C. and Lau, L. J. , 1998, "The China-United State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How Big Is It Really?".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3(1), 33–47. DOI:10.1111/per.1998.3.issue-1 |
| [] | Fung, K. C. and Lau, L. J. , 2003, "Adjusted Estimates of United States-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1995-2002".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4(1), 489–496. |
| [] | Hummels, D. , Ishii, J. and Yi, K ,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1), 75–96. DOI:10.1016/S0022-1996(00)00093-3 |
| [] | Koopman, R. Powers. Wang Z and Wei SJ., 2010,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Chains"NBER Working Paper No.16426. |
| [] | Koopman, R. , Wang, Z. and Wei, SJ. , 2014,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 459–94. DOI:10.1257/aer.104.2.459 |
| [] | Martin Neil Baily, Robertz. Lawrence., 2004, "What Happened to the Great U. S. Job Machine? The Role of Trade and ElectronicOffshoring"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 |
| [] | Marcel P.Timmer、Bart Los、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de Vries., 2013, "Fragmentation, Incomes and Jobs.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paper for the 57th Panel Meeting of Economic Policy. |
| [] | Neil Foster、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de Vries., 2011, "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factor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WIOD Working Paper No. 225281. |
| [] | Samuelson, Paul A. 2004,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 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Globaliz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3), 106–132. |
| [] | Robert E.Scott., 2005, "US-China Trade, 1989-2003:Impaction jobs and industries, nationally and state-by-stat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270. |
| [] | Robert E.Scott, 2008, "China trade costs jobs in every state"EPI.Economic snapshot for July 30. |
| [] | LawrenceJ.Lau, 2007, 《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 《中国社会科学》, 第 5 期, 第 91–103 页。 |
| [] | 黄先海, 2010,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 《世界经济》, 第 5 期, 第 82–100 页。 |
| [] | 黎峰, 2014,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贸易收益及核算——基于中国的实证》, 《国际贸易问题》, 第 6 期, 第 14–22 页。 |
| [] | 黎峰, 2015,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收益——基于主要出口国家的行业数据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第 6 期, 第 33–42 页。 |
| [] | 刘光溪、陈文刚, 2006, 《中美贸易失衡的最大得益者: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兼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得益情况》, 《国际贸易》, 第 7 期, 第 4–9 页。 |
| [] | 刘建江、杨细珍, 2011,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第 8 期, 第 68–80 页。 |
| [] | 沈国兵, 2005, 《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经济研究》, 第 6 期, 第 82–93 页。 |
| [] | 宋玉华、陈喆, 2002, 《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11 期, 第 60–65 页。 |
| [] | 孙天阳、许和连、吴刚, 2014, 《基于复杂网络的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格局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 2 期, 第 19–42 页。 |
| [] | 王苍峰、王恬, 2009, 《对中美贸易条件恶化的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第 8 期, 第 31–35 页。 |
| [] | 王岚、盛斌, 2014,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 《财经研究》, 第 6 期, 第 97–108 页。 |
| [] | 于津平、邓娟, 2014, 《垂直专业化、出口技术含量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 2 期, 第 44–63 页。 |
| [] | 尹翔硕, 2001, 《进入新经济时期的美国贸易逆差——兼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世界经济研究》, 第 2 期, 第 48–53 页。 |
| [] | 曾铮、张路路, 2008,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第 1 期, 第 36–43 页。 |
| [] | 张咏华, 2013,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与中美贸易失衡》, 《财经研究》, 第 2 期, 第 15–2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