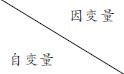创新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桎梏。根据一般理解,中国企业在经济发展初期的研发投入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当时的禀赋条件约束,即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倾斜,由此导致了工业部门整体研发投入水平的低下。然而从动态视角来看,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已悄然发生转变。仅从资本劳动两大基本要素来看,中国工业部门内部资本-劳动比率已经由2000年的22.70万元/人上升到了2011年的73.72万元/人①,由此呈现出了一定的资本深化特征。但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禀赋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资本深化似乎并未带来企业研发投入的显著增加,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 & D投入占增加值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始终徘徊于2%-3%左右①。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在资本深化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依旧踟蹰不前呢?一些早期研究试图从市场结构(Arrow,1962)、企业规模(Pavit et al., 1987;Freeman and Soete, 1997) 等内外部因素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但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些传统因素显然不足以对上述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
从根本上来看,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企业管理者在一定的制度规则下所做出的利益最优决策的结果,这意味着制度环境在激发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方面发挥着更为根本性的影响。为此,一些学者分别从产权保护(Branstetter,2006;Schneider,2005;邓海滨和廖进中,2009);产权结构(Jefferson,2004;李春涛和宋敏,2010;吴延兵,2007);融资效率与融资约束(Aghion and Howitt, 1998;王永齐,2007;唐清泉和肖海莲,2012);政府干预(Marcus and Howard, 2003;安同良等,2009);社会关系资本(Tsai,2006;Yli-Renko et al., 2001;Weber and Christiana, 2007;韦影,2007) 以及公司治理(范海峰和胡玉明,2012) 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但这些有关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仍集中于那些“普遍”或“共性”的制度安排,而鲜有涉及中国因渐进式的经济转轨而呈现出的某些“非正统”的制度安排,在这其中,因要素配置的非市场化而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
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无疑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现象(盛仕斌和徐海,1999),政府对各类要素分配权和定价权的控制使得中国要素价格存在着明显的扭曲,这已得到了很多研究(如Hsieh, Klenow,2009;罗德明等,2012;施炳展和冼国明,2009;史晋川和赵自芳,2007;邵敏和包群,2012) 的证实。这种扭曲的存在不仅会通过引发“资源错配”引起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降低(Hsieh,Klenow,2009;罗德明等,2012),甚至会通过激励企业家过度使用有形要素乃至寻租行为降低研发活动的动机(张杰等,2011)。然而纵观目前的研究文献,直接将中国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与国内企业创新动机问题相联系的文章仍基本处于空白。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地区宏观经济视角出发,利用以DEA为基础的非参数估计对各地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进行重新测度,并在对地区研发强度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检验了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产业结构以及产业链层级对区域总体研发强度所产生的影响,以此形成对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研发活动间关系的完整认识。
二、 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的测算劳动力价格扭曲是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表现。很多学者曾从理论上指出这种扭曲背后的制度根源,如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流动壁垒 (Chan, Henderson and Tsui, 2009;Demurger et al., 2009);体制性因素以及歧视性因素(谢嗣胜和姚先国,2006) 都会导致要素实际收入偏离其边际贡献。但在扭曲程度测算方面,现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做法。一些研究倾向于使用宏观代理指标,如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或非正规就业人数(胡凤霞和姚先国,2011) 以及市场化进程指数(张杰等,2011) 等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的反映,但此类方法显然缺乏足够的针对性;相对而言,另一些研究则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利用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实际回报的比较来测度要素价格的扭曲,但在具体测度方法上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C-D函数法(施炳展和冼国明,2009)、超越对数函数法(史晋川和赵自芳,2007) 以及投入产出表法(邵敏和包群,2012)。
基于不同方法的测度从多个视角证实了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存在性。然而从更为客观的角度来看,目前对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度仍存在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明确要素的边际产出水平是确定要素价格是否“合理”的重要前提,目前各类研究大都通过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并依靠对样本的回归分析来确定要素的边际产出,但出于简化分析起见,很多研究往往假设各生产单位(地区) 的生产函数具有统一的参数结构,而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生产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差异,这种简化显然会忽略地区之间生产函数形式的差异并导致结果的偏差。其次,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是决定企业产品结构乃至生产方式的关键,现有研究大多证实,中国的各类要素(如资本、劳动等) 价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负向扭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判断单一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显然不足以为解释中国企业研发行为提供充足的依据,判断各类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也应当成为更合理的选择。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测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扭曲的过程中延续了现有研究以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实际回报之间差异来度量要素价格扭曲的基本思路,但在具体的测度方法上采用了变参数的估计方法,同时,测度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了劳动力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方面,以此为进一步分析和判断劳动力价格扭曲与企业研发行为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
(一) 基准模型假定地区i的工业部门服从中性技术进步且规模收益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生产使用资本K与劳动力L两种要素,则有Yi=AiKiαiLi1-αi,其中Yi为地区i的产出,αi为资本产出弹性。另设地区i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报酬率分别为wi与ri①,则该地区面临的产出最大化问题为:
① 为剔除政府税收因素影响,假定此报酬率均为税前报酬率。
| $\begin{array}{*{20}{c}} {Max\{ {A_i}K_i^{{\alpha _i}}L_i^{1 - {\alpha _i}}\} }&{\begin{array}{*{20}{c}} {s.t.}&{{w_i}{L_i} + {r_i}{K_i} = {A_i}K_i^{{\alpha _i}}L_i^{1 - {\alpha _i}}} \end{array}} \end{array}$ | (1) |
由该最大化问题一阶必要条件可得:
| $\frac{{{\alpha _i}}}{{1 - {\alpha _i}}} = \frac{{{r_i}{K_i}}}{{{w_i}{L_i}}} = \frac{{{Y_i} - {w_i}{L_i}}}{{{w_i}{L_i}}}$ | (2) |
(2) 式给出了在要素投入效率最优情况下劳动力要素报酬总额与资本产出弹性之间的关系。设经济体中劳动要素的“合理”报酬水平
| ${{\bar P}_i} = ({Y_i} - {{\bar S}_i})/{{\bar S}_i} = {\alpha _i}/(1 - {\alpha _i})$ | (3) |
另设劳动者实际获得的报酬水平为Si,则劳动要素相对资本要素的实际价格Pi为:
| ${P_i} = ({Y_i} - {S_i})/{S_i}$ | (4) |
由此可定义该地区要素价格相对价格扭曲程度DISi为:
| $DI{S_i} = (\frac{{{P_i} + 1}}{{{{\bar P}_i} + 1}}) = \frac{{(1 - {\alpha _i}){Y_i}}}{{{S_i}}}$ | (5) |
作为资本相对劳动要素实际价格与合理价格之间的偏差,DISi可以作为度量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度量标准。当DISi>1时,表明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要素的实际价格高于理论价格,意味着经济中存在着资本要素价格的相对高估或劳动要素价格的相对低估;反之当DISi<1时,则表明经济中存在着资本要素价格的相对低估或劳动要素价格的相对高估。
(二) 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测度结果(4) 式给出了特定生产函数形式和参数下地区劳动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测度公式。根据此公式,在经济体的产出水平Yi与工资总量Si明确的情况下,合理的确定资本产出弹性α是准确度量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关键。由于要素扭曲指标的确定以C-D生产函数设定为前提,为了保持分析的逻辑一致性,对于资本产出弹性α的测算也以基于C-D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来进行。为了刻画因产业结构等因素导致的生产函数地区差异性,我们假设各地区的生产函数具有不同的资本产出弹性αi,但各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在时间维度上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以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地区实际工业增加值度量产出Yi,以经永续盘存法进行价格调整后的地区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存量和地区工业部门从业人数分别度量资本要素投入Ki①和劳动要素投入Li,对C-D函数的对数变换方程(6) 式进行变参数的时间固定效应pool模型估计得到地区资本产出弹性αi。②
① 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价格调整如下:以地区i工业企业各时期的固定资产年末余值之差(扣除折旧影响) 作为当年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即ΔKti=Kti-(1-σ)Kt-1i,其中σ为每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实际计算中取5%)。设第t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定基指数为PtK,则第t年的固定资产实际存量为:
② (6) 式回归结果为:ln(Yit/Lit)= αiln(Kit/Lit)+0.3370+ui, t, (R2=0.9497 adjusted R2=0.9436 s.e. 0.1399),各地区资本产出弹性结果详见表 1。
| ${\rm{ln}}({Y_{i,{\rm{ }}t}}/{L_{i,{\rm{ }}t}}) = {\alpha _i}{\rm{ln}}({K_{i,{\rm{ }}t}}/{L_{i,{\rm{ }}t}}) + {\rm{ln}}({A_{i,{\rm{ }}t}}) + {u_{i,{\rm{ }}t}}$ | (6) |
其中ui, t为随机误差项。计算样本中各地区增加值数据、固定资产存量数据、从业人员数据均源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在得到地区资本产出弹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所载各地区工资总量数据作为实际工资总额Si的指标,可计算得各地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情况如表 1。
根据表 1,中国各地区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指数基本上处于高于1的水平,表明我国经济整体上呈现出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价格被低估的扭曲特征。从这种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地区分布看,2001年除内蒙古和湖南外其他地区均表现为资本价格的相对高估或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估,2011年则全部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低估,而且以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劳动力价格低估程度更为严重。从动态演进来看,相对于2001年而言,除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个省市之外,其它地区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低估程度均呈现一定的恶化趋势,表明我国大部分地区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低估程度仍处于不断扩大的进程当中。
| 表 1 中国各地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测算结果 |
相关测算结果证实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相对低估倾向。这种劳动力价格的相对负向扭曲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工业部门在资本深化背景下研发投入动力不足的问题。
(一) 禀赋结构与R & D投入从宏观层面来看,要素禀赋结构至少从如下三方面决定地区工业部门的整体研发投入意愿。
首先,从产品结构来看,要素禀赋结构是形成地区产品结构的基础。特别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这意味着资本丰裕度相对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会形成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普遍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因此这种产业结构变化也会引起该国家或地区工业部门整体研发投入水平的增加。进一步从动态角度来看,依据罗伯津斯基定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要素出现相对增长时,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出也会随之扩大,由此引起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其次,从产业链结构来看,要素禀赋同样决定了相关产业在各自的产业链上所处的层级。随着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加强,特定产业的生产过程也越来越多的被划分为由研发、核心部件制造、外围零部件制造、加工组装和销售等相对独立的环节,由此导致了国际分工格局逐渐由传统的产品分工向产业链分工演进。参与分工的地区尽管在广义层面上从事同一种产业的生产,但其在产业链条上所处的地位却往往存在很大差别,而要素禀赋则是决定或地区在相关产业链层级中所处地位的关键。一般而言,充裕的资本要素会对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研发与核心部件制造等环节形成吸引,因此当要素禀赋结构出现偏向资本要素的增长变化时,该地区工业部门整体的研发投入水平也会随着其所从事的产业链层级的上移而出现显著的增加。
再次,从产品的具体生产工艺来看,要素禀赋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内部要素配置与生产方式。当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存在一定的可替代性时,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企业也可能因要素配置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地区而言,由于劳动力的稀缺性和高成本,企业往往会利用更多的资本要素来替代劳动力要素,而这种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实际上表现为现代工业生产对“自动化”的追逐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工艺的变革,而这一追逐与变革的过程则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
(二) 劳动力价格扭曲下的资本深化与企业R & D投入以资本深化为特征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可以通过改变相关地区的产品结构、产业链结构乃至具体的生产方式来提升本地工业部门的研发投入水平,但这种激发效果却是借助于要素价格的改变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一个充分市场化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是决定禀赋改善能否激发企业R & D投入提升的重要前提。然而,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诸多扭曲使得我国的劳动力价格长期处于相对低估的扭曲状态,要素市场的价格显然无法准确的反映出我国禀赋结构的调整,这无疑阻断了禀赋结构变化所引发的资本深化与工业部门研发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至少从如下五方面对工业部门的研发投入行为形成了阻滞。
第一,从地区的产品结构来看,劳动力要素相对价格的低估会夸大当地劳动力的相对丰裕程度,使得该地区“现实”的比较优势并不符合当地自身的禀赋状况。这种由劳动力价格相对低估导致的对劳动力禀赋的夸大会令相应地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过度的吸引,使得当地的产业结构长时间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当地工业部门的研发投入也自然无法随禀赋结构的变化而实现应有的提升。
第二,从地区相关产业所处的产业链层级来看,劳动力要素价格的相对低估同样会对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加工组装等生产环节产生吸引,造成该地区相关产业的生产活动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低端环节,而无法向具有更多资本密集型色彩的研发创新以及核心部件制造等高端环节延伸,由此也进一步限制了工业部门的研发创新活动。
第三,从企业内部的生产方式来看,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估也会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倾向于使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要素来替代资本要素,由此降低了对资本要素以及附着于资本品之上的技术创新的需求,并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的动力。
第四,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环节乃至生产方式往往因具有较低的技术门槛而在呈现出更强的竞争性,因此从事相关生产的企业也无法获得更为丰厚附加值和利润回报。而在劳动力价格低估的背景下,由于大量的企业被廉价的劳动力要素吸引而被局限于劳动密集型领域,其盈利水平与附加值都会处于相当低下的情况,这也使得相关企业无力在研发创新方面做出更多的投入。
第五,从劳动力价格相对扭曲的背景根源来看,作为非市场化程度的反映,这种扭曲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于土地、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关键要素的主导和控制。在政府掌握了关键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的背景下,企业如果能够和政府官员建立某种寻租联系,就可以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相对低成本的资金和其他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这种价格扭曲的存在本身意味着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寻租收益(张杰等,2011)。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投资与政府建立寻租联系获得超额利润或寻租收益,还是通过对R&D 投入来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从而获得创新超额利润就成为了企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选择。而很多研究(如Murphy et al,1993) 均曾指出,在那些广泛存在寻租机会的经济体中,企业会更有动力投资于寻租活动。寻租活动产生的超额收益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才从实体投资领域转移到非生产的寻租活动中去,从而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等实体投资活动产生转移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而导致该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动力下降。
四、 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与地区工业研发强度:实证检验中国要素市场存在的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会从产品结构、产业链层级、生产方式以及激发寻租活动等诸多方面对企业的研发活动形成阻滞,进而使得中国的工业部门在资本深化的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依然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我们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地区工业数据对劳动力价格扭曲、资本深化与工业研发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一) R & D投入强度及其分解由于地区总体的R & D强度变化主要源自地区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内部的产业链层级与生产工艺状况,而要素价格扭曲对地区工业部门R & D强度的影响也主要通过产业间与产业内两条基本途径来得以实现。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各地区工业部门R & D强度变化的基本动因以及要素价格扭曲在其中产生的具体影响,我们首先对地区工业部门的R & D强度指标进行相应的分解。
记地区i在时期t的工业增加值为
| ${R_{i,{\rm{ }}t}} = {r_{i,{\rm{ }}t}}/{Y_{i,{\rm{ }}t}}$ | (7) |
记行业j在地区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是
| $St{r_{i,{\rm{ }}t}} = \sum {_{j = 1}^J} (s_{i,{\rm{ }}t}^j*R_{A,0}^j) = \sum {_{j = 1}^J} (r_{A,0}^jY_{i,{\rm{ }}t}^j/Y_{A,0}^j)/{Y_{i,{\rm{ }}t}}$ | (8) |
Stri, t值越高,表明具有R & D活动的行业在地区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越高,反之,Stri, t值越低,则表明具有R & D活动的行业在地区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越低。
从产业内部的产业链层级与生产工艺角度来看,不妨将行业j本身在基期时的全国平均R & D投入强度RA, 0j视为基准水平,因此RA, 0j*Yi, tj可视为地区在使用该基准研发强度时的理论R & D投入量,并令
| $Lin{k_{i,{\rm{ }}t}} = {r_{i,{\rm{ }}t}}/{{\bar r}_{i,{\rm{ }}t}} = {r_{i,{\rm{ }}t}}/\sum {_{j = 1}^J} (r_{A,0}^jY_{i,{\rm{ }}t}^j/Y_{A,0}^j)$ | (9) |
Linki, t值越高,表明工业部门在相同的产业结构下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即工业部门在产业内部位居更高的产业链层级或更倾向于采用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工艺;反之,如果Linki, t较低,则意味着当地的工业部门在产业内部位于更低端的产业链层级,或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工艺。
根据式(8)、(9) 可知:
| ${R_{i,{\rm{ }}t}} \equiv {r_{i,{\rm{ }}t}}/{Y_{i,{\rm{ }}t}} \equiv St{r_{i,{\rm{ }}t}}*Lin{k_{i,{\rm{ }}t}}$ | (10) |
因此,地区工业R & D投入强度变化可分解为地区产业结构因素和产业链层级因素。
根据式(7)~(9) 以及各地区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后的工业企业实际R & D投入量ri, t和行业增加值Yi, tj,计算中国各地区在样本期(2001-2011) 内R & D投入强度及影响因素如表 2所示。其中,各地区R & D投入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①。
①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对于工业部门R & D活动的统计口径历年并不统一,其中2001-2003、2005-2007以及2009-2010年统计口径为大中型工业企业,2004、2008、2009与2011年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于2009年同时披露了规模以上以及大中型企业相关数据,我们以此为基础计算了两类口径之间R & D支出的相对比率,并据此估算了2004、2008以及2011年大中型企业的R & D支出情况,将全部样本点的研发支出数据统一到大中型企业。鉴于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支出普遍占到了当地研发支出总额的80%以上,因此以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支出作为当地企业研发支出的代理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表 2 工业企业R & D投入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
根据表 2数据,中国各地区工业企业R & D投入强度均低于0.8%,并且地区之间差距较大,以北京和海南为例,二者差距超过4倍。在2001年-2011年内,企业R & D投入强度增加的地区仅有10个,其余地区的R&D投入强度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弱。就产业结构而言,有16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改善,11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不同程度恶化,3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未出现明显改变。此外,有10个地区实现产业链结构的提升,其余20地区的产业链与生产工艺水平未实现提高。
(二) 模型设定如前所述,要素禀赋则可以通过影响地区的产业间结构与产业内部的产业链地位及生产方式来改变当地工业部门的研发强度。因此,要全面反映要素禀赋以及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对企业R & D投入强度的影响,有必要对地区产业结构和技术状况的影响进行相应的区分。除了要素价格因素之外,其它一些地区宏观经济、行业特征以及企业特征因素,如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以及所有制结构等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当地的产业结构乃至产业链和生产工艺而改变当地工业部门的研发投入状况,因此在考察中也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必要的控制。
基于上述两方面问题,考虑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检验模型:
| ${\rm{ln}}(R{D_{i,{\rm{ }}t}}) = {\alpha _1}{\rm{ln}}(P{K_{i,{\rm{ }}t}}) + {\alpha _2}{\rm{ln}}(Di{s_{i,{\rm{ }}t}}) + {\theta _k}\sum {_{k = 1}^K} X_{i,{\rm{ }}t}^k + C + {u_{i,{\rm{ }}t}}$ | (11) |
| ${\rm{ln}}(St{r_{i,{\rm{ }}t}}) = {\beta _1}{\rm{ln}}(P{K_{i,{\rm{ }}t}}) + {\beta _2}{\rm{ln}}(Di{s_{i,{\rm{ }}t}}) + {\varphi _k}\sum {_{k = 1}^K} X_{i,{\rm{ }}t}^k + C + {u_{it}}$ | (12) |
| ${{\rm{ln}}\left( {Lin{k_{i,{\rm{ }}t}}} \right) = {\gamma _1}{\rm{ln}}\left( {P{K_{i,{\rm{ }}t}}} \right) + {\gamma _2}{\rm{ln}}\left( {Di{s_{i,{\rm{ }}t}}} \right) + {\eta _k}\sum {_{k = 1}^K} X_{i,{\rm{ }}t}^k + C + {u_{it}}}$ | (13) |
方程(11) 主要考察要素禀赋结构以及价格扭曲对地区总体研发强度的影响。方程以地区产业结构指数Stri, t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部门要素禀赋结构,即人均资本存量PKi, t和要素价格扭曲程度Disi, t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在方程中纳入K个可能对当地产业结构形成影响的控制变量Xi, tk。
方程(12) 与(13) 主要考察要素禀赋以及价格扭曲对当地产业结构及产业链层级等产生的影响。方程分别以产业结构指数Stri, t和以产业链层级指数Linki, t为被解释变量;同样以地区工业部门要素禀赋结构PKi, t和地区工业部门面临的要素价格扭曲Disi, t为核心解释变量;为控制其他可能对地区工业部门研发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在方程中纳入其它K个可能对当地产业结构形成影响的控制变量Xi, tk。
方程中纳入的控制变量Xi, tk包括三类:一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地区人均生产总值Pgdpi, t度量;二是地区市场化程度,考虑以国有企业在当地工业部门所占比重Soei, t和外资企业在当地工业部门所占比重Fdii, t,以及地区R & D投入对财政资金的依存度Govi, t来度量;三是企业特质性差异,包括企业规模Sizei, t、盈利能力Earni, t、固定资产装备率Capi, t和人力资源存量Hri, t。此外,在方程(17) 中引入企业规模与资本密集度二次项以检验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
进一步考虑要素价格扭曲可能会抑制地区以资本深化为特征的要素结构调整对当地工业部门产业结构以及产业链层级的影响,为此考虑在基本方程(11)~(13) 的基础上加入人均资本存量Pk与要素价格扭曲Dis的交互项,以此检验要素扭曲与人均资本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而明确在要素价格扭曲时禀赋结构对地区整体研发投入起到的真正作用。由此形成检验方程如下:
| ${\rm{ln}}(R{D_{i,{\rm{ }}t}}) = {\alpha _1}{\rm{ln}}(P{K_{i,{\rm{ }}t}}) + {\alpha _2}{\rm{ln}}(Di{s_{i,{\rm{ }}t}}) + {\alpha _3}{\rm{ln}}(P{K_{i,{\rm{ }}t}})*{\rm{ln}}(Di{s_{i,{\rm{ }}t}}) +\\ {\theta _k}\sum {_{k = 1}^K} X_{i,{\rm{ }}t}^k + C + {u_{i,{\rm{ }}t}}$ | (14) |
| ${\rm{ln}}(St{r_{i,{\rm{ }}t}}) = {\beta _1}{\rm{ln}}(P{K_{i,{\rm{ }}t}}) + {\beta _2}{\rm{ln}}(Di{s_{i,{\rm{ }}t}}) + {\beta _3}{\rm{ln}}(P{K_{i,{\rm{ }}t}})*{\rm{ln}}(Di{s_{i,{\rm{ }}t}}) +\\ {\theta _k}\sum {_{k = 1}^K} X_{i,{\rm{ }}t}^k + C + {u_{i,{\rm{ }}t}}$ | (15) |
| ${\rm{ln}}(Lin{k_{i,{\rm{ }}t}}) = {\gamma _1}{\rm{ln}}(P{K_{i,{\rm{ }}t}}) + {\gamma _2}{\rm{ln}}(Di{s_{i,{\rm{ }}t}}) + {\gamma _3}{\rm{ln}}(P{K_{i,{\rm{ }}t}})*{\rm{ln}}(Di{s_{i,{\rm{ }}t}}) +\\ {\theta _k}\sum {_{k = 1}^K} X_{i,{\rm{ }}t}^k + C + {u_{i,{\rm{ }}t}}$ | (16) |
其中系数α3、β3与γ3分别度量了要素价格扭曲对资本深化的研发促进效应的影响,若该系数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存在较高的要素价格扭曲时以资本深化为特征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动不会引起当地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层级积极变化,从而无助于工业部门研发水平的提升。
(三) 指标构建与样本选择模型中相关指标的构建与样本选择情况如下:
被解释变量RDit、Strit与Linki, t分别以此前计算所得的地区与研发强度,以及由此分解所得相关的产业结构指数和产业链层级指数衡量;此外,以“地区资本存量估计值具体①/地区人口总数”与前文计算的地区工业部门要素价格扭曲指数DIS作为人均资本存量PKi, t和要素价格扭曲程度Disi, t这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指标。
① 方法为:以地区i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Iti作为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设σ为每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实际计算中取5%),PtK为第t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定基指数,则第t年的固定资产实际存量为:
其它控制变量的指标构建方式如下:
(1) 人均生产总值Pgdpi, t:以经GDP平减指数平减后的“实际GDP/地区总人口”衡量。
(2) 国有企业比重Soei, t: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衡量。
(3) 外资企业比重Fdii, t:以“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衡量。
(4)R & D投入市场化程度Govi, t:以“R & D筹资中财政来源部分/R & D总筹资额”衡量。
(5) 企业规模Sizei, t:以企业平均固定资产净额衡量。
(6) 企业盈利能力Earni, t:以企业当期人均利润额衡量。
(7) 固定资产装备率Capi, t:以“固定资产净值/年末在岗职工人数”衡量。其中固定资产净值经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平减后的固定资产实际值,具体调整方法同前(脚注1)。
(8) 人力资本存量Hri, t:以地区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比重为代理变量。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2001年—2011年中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台湾省、西藏除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各地区分行业数据及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如表 3所示。
| 表 3 变量统计描述 |
为了克服地区之间的个体差异,降低截面异方差性,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 模型中的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4所示。
| 表 4 估计结果 |
方程(11)~(13) 体现了禀赋结构变化以及要素价格扭曲对地区研发强度以及产业结构与产业链层级所产生的影响。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水平仅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微弱的正向影响,对产业链层级的影响不甚显著,由此对地区工业部门的研发强度也仅产生了有限的促进作用,这也从一定侧面反映了经济中存在的诸多体制性扭曲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而从地区工业部门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受目前研发活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影响,目前地区产业结构乃至产业链的升级仍带有相当的政府主导色彩,并主要通过与政府关联更为密切的国有企业来完成,而国有企业也凭借其在融资成本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产业链结构升级乃至整体研发投入起到了显著的证明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对于本地工业部门研发强度的影响略微复杂:一方面,受各地方政府现行以产业划分为依据的招商引资政策的影响,相当部分的外资企业进入到了具有更高研发密集度的行业,进而导致了外资企业的流入对本地的产业结构向研发密集型转移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要求,更多在华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仍然将中国作为加工组装的基地,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高新技术”行业中从事着低端的生产活动,由此造成了外资企业的进入显著降低了当地工业部门的产业链层级,综合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本地工业部门的研发投入并无显著的作用。进一步从研发投入本身的市场化程度来看,回归方程的结果表明,政府资金在研发活动中的比重增加似乎并没有带来当地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层级的有效提升,由此意味着以政府为主导的研发体制并不会对当地工业企业的研发强度起到显著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从工业部门本身的特征来看,企业规模对于地区工业研发强度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即当企业规模低于一定临界水平时,企业规模的提升会因其资本实力与竞争力的增强带来企业研发动机的增加,但当企业规模高于临界点时,则会因垄断力量的存在而削弱其通过技术进步追求利润的动机,由此弱化了对研发活动的需求。进一步而言,这种非线性效应更多的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得到表现,而在产业链升级方面,企业规模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企业固定资产装备率同当地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与产业链层级存在明显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当企业的产业链层级由简单的加工组装向深层次的核心部件制造领域扩展时,可能会因为生产工艺的要求而增加相应的固定资产配备,但当企业的产业链层级过渡到了研发环节后,对于固定资产配备的要求则会相应弱化。就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来看,其主要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产业链层级乃至地区工业部门整体研发投入影响并不显著。
上述结果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意义上能够激发企业研发活动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盈利因素以及人力资本状况在我国均没有能够发挥出理想的效果,方程(10)~(12) 中禀赋结构变量PKi, t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现象,在顾及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后可以发现,资本深化并没有能够带来产业结构以及产业链层级的明显提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产生了“降级”的效应,并由此对于当地的研发强度未能产生显著性的影响。究其原因,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融资约束以及要素扭曲等体制性障碍可能是导致企业在经济发展、规模与盈利能力扩张情况下依然缺乏研发动机的内在根源,而方程中要素价格扭曲变量Disi, t的回归结果则印证了我们这一判断,从回归结果来看,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在更具市场化特征的产业链层级与生产工艺方面,由于政府无法通过产业政策导向在该领域进行引导和干预,要素价格扭曲在其中抑制作用也有着更为强烈的表现。综合上述两方面情况,国内要素市场所存在的低估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无疑是导致地区工业部门整体研发投入力度不足的重要制度根源。
方程(14)~(16) 分别在原方程中加入了人均资本存量与要素价格扭曲变量的交互项,以此来解答本文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即要素价格扭曲是否是导致资本深化没有产生明显的研发促进效果的原因。在加入了该连乘变量后方程(15) 的交互项Pkit*Disit的系数显著性稍弱,其原因可能是政府的产业导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负面作用;但方程(16) 中交互项Pkit*Disi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越严重,资本深化对地区产业链升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则越不明显。综合两方面效应,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是阻碍地区工业部门整体研发强度提升的显著性因素。进一步而言,考虑到禀赋结构变量Pkit与要素价格扭曲Disit的交互影响后,地区人均资本存量本身对产业结构、产业链升级乃至研发强度都会呈现出更为明显促进作用。换而言之,如果消除了各地区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现象,则以资本深化为特征的禀赋结构调整对技术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有更为明显的表现。由此可以证实,要素价格扭曲的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低估确实是导致中国工业部门在资本深化背景下依然缺乏研发投入动机的重要原因。
五、 基本结论本文主要从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深化背景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依然乏力这一基本问题出发,从中国要素市场存在的价格扭曲入手分析了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估对于地区工业部门研发投入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对地区工业研发强度指标的分解,从产业结构与产业链层级两方面检验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地区工业研发强度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检验,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中国的要素市场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价格扭曲,这种价格扭曲集中的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低估,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受制于歧视性的融资环境带来的资本价格高企以及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低估,这种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在近年来呈恶化倾向。
其次,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可以通过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内部的产业链层级与生产工艺来提升当地工业部门整体的研发投入水平,但这一效应的显现要以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为基本前提,只有在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下,要素价格的变化才能够正确的体现要素禀赋结构的调整,进而通过改变当地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与产业链层级来激发工业部门整体的研发投入。
再次,近年来,尽管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竞争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禀赋结构也出现了以资本深化为特征的显著调整,但各地区工业企业R & D投入强度始终停滞不前。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则恰恰在于中国要素市场所存在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于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这种扭曲的存在不仅直接阻碍了地区产业结构与产业链层级的升级调整,而且也弱化了资本深化对研发相关的产业结构与产业链层级调整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工业企业的R & D投入并未呈现与资本深化相一致的增强趋势。
最后,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现行以产业划分为基础的产业导向政策影响,要素价格扭曲对于产业结构层面的负面效应表现得不甚明显,但在更具市场化特征的产业链层级与生产工艺层面,要素价格扭曲则会起到相当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行的产业导向政策固然会带来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如果不能理顺经济中存在的制度性扭曲,这种政府导向的“强制性”升级却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地区研发投入的增加和地区工业生产活动在真正意义上的高端化。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解除要素市场的各种壁垒与限制,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应当成为促进国内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着力点。
| [] | Aghion P., P. Howitt, 1998,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Proces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1), 276–305. DOI:10.1006/redy.1997.0007 |
| [] | Arrow K.J, 1962,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n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ds. by Nelson P.R., pp.609-626, Published by NBER. |
| [] | Branstetter L.G., R. Fisman and C.F.Foley , 2006, "Do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reas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S firm-level panel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321–349. DOI:10.1093/qje/121.1.321 |
| [] | Chan, Kam-Wing, J. V. Henderson and Kai-Yuen Tsu, 2009, “Spati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s. by Brandt, L. and G. T. Rawski, pp. 776-828,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 | Fare, R., S. Grosskoff and C.A. Lovell, 1994, Production Frontiers,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 | Freeman, C. and L. Soete,1997,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Published by Routledge Press. |
| [] | Hsieh C.T., P.J. Klenow, 2009, "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DOI:10.1162/qjec.2009.124.4.1403 |
| [] | Jefferson G.H., H.M. Bai, X.Y. Guan and X.Y YU, 2004, " R & 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13(1/2), 345–366. |
| [] | Marcus N. and P. Howard, 2003, “Industrial Polic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Asi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
| [] | Murphy K.M., A. Shleifer and R. Vishy, 1993, "Why is Rent-Seeking Costly to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2), 409–414. |
| [] | Pavitt K., M. Robson. and J. Townsend, 1987,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ng Firms in the UK: 1945 —1983,".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35, 297–316. DOI:10.2307/2098636 |
| [] | Schneider PH, 2005,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Panel Data Study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8(2), 529–547. DOI:10.1016/j.jdeveco.2004.09.001 |
| [] | Tsai Y, 2006, "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in Internet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 157–166. |
| [] | Weber B., W. Christiana, 2007, "Corporative Venture Capital as a Means of Radical Innovation: Relational fit,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Transfer,".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4, 11–35. DOI:10.1016/j.jengtecman.2007.01.002 |
| [] | Yli-Renko H., E. Autio and H. Sapienza, 2001,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Exploitation in Young Technology-based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578–613. |
| [] | 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 2009, 《R & 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 《经济研究》, 第 87–98,120 页。 |
| [] | Demurger、Fournier、李实、魏众, 2009, 《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不同部门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 《管理世界》, 第 3 期, 第 55–64 页。 |
| [] | 邓海滨、廖进中, 2009, 《制度安排与技术创新:基于负二项式模型的研究》, 《科学学研究》, 第 7 期, 第 1101–1109 页。 |
| [] | 范海峰、胡玉明, 2012,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研发支出——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南方经济》, 第 9 期, 第 60–69 页。 |
| [] | 何枫、陈荣、何林, 2003, 《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和相关分析》, 《经济学家》, 第 5 期, 第 29–35 页。 |
| [] | 胡凤霞、姚先国, 2011, 《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 第 191–199 页。 |
| [] | 李春涛、宋敏, 2010,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CEO激励的作用》, 《经济研究》, 第 5 期, 第 55–67 页。 |
| [] | 罗德明、李晔、史晋川, 2012, 《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 《经济研究》, 第 4–14,39 页。 |
| [] | 邵敏、包群, 2012, 《外资进入是否加剧中国国内工资扭曲: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 《世界经济》, 第 10 期, 第 3–24 页。 |
| [] | 盛仕斌、徐海, 1999, 《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 《经济研究》, 第 5 期, 第 68–74 页。 |
| [] | 施炳展、冼国明, 2012, 《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 《中国工业经济》, 第 2 期, 第 47–56 页。 |
| [] | 史晋川、赵自芳, 2007, 《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统计研究》, 第 6 期, 第 42–47 页。 |
| [] | 唐清泉、肖海莲, 2012,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基于企业R & D异质性视角》, 《南方经济》, 第 11 期, 第 40–54 页。 |
| [] | 王永齐, 2007, 《融资效率、劳动力流动与技术扩散: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的经验检验》, 《世界经济》, 第 1 期, 第 69–80 页。 |
| [] | 韦影, 2007, 《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第 9 期, 第 119–127 页。 |
| [] | 吴延兵, 《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R & D——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统计研究》, 第 5 期, 第 67–75 页。 |
| [] | 谢嗣胜、姚先国, 2006, 《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第 4 期, 第 49–55 页。 |
| [] | 张杰、周晓艳、李勇, 2011,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 & D?》, 《经济研究》, 第 8 期, 第 78–9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