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发现前后
)的发现前后
1950年前后,关于基本粒子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验手段都已初步具备。相应地,粒子物理作为一个学科从原子核物理中独立出来,渐臻成熟。而当时的中国,虽有一批在欧美受过核与粒子物理学教育并参与过前沿研究工作的学者先后回国,但因国内科技、经济基础的薄弱,高能实验物理受仪器、设备之限,基本付之阙如。直至1980年代后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这种状态才得到根本改变。而在此三四十年间,中国学者仍有一项享誉世界的高能实验成就,就是王淦昌等在苏联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反西格马负超子( )的发现。60年后回顾这项工作,结合当时的国际科学背景与中国亚原子物理实际水平,以及该发现的后续影响,希望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这项工作乃至中国学者在杜布纳系列科学研究对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意义。
)的发现。60年后回顾这项工作,结合当时的国际科学背景与中国亚原子物理实际水平,以及该发现的后续影响,希望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这项工作乃至中国学者在杜布纳系列科学研究对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意义。
诚如很多科学史家与物理学家所言,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而粒子物理学则是20世纪后半叶最耀眼的物理学分支。在 发现之前,基本粒子研究已经获得了多方面的重要进展。
发现之前,基本粒子研究已经获得了多方面的重要进展。
在1930年代初原子核物理学诞生之际,电子、光子、质子、中子先后被物理学家发现。质子、中子构成原子核,再与电子构成原子,然后构成实体物质;而光子可以解释电磁辐射与能级跃迁。如此,无需其他粒子,便足以形成自然界的物质大厦了。“基本粒子”的概念逐渐形成,如S.温伯格所言,是“表面看来不能进一步分割的微小单元” [1]。可此后,μ子、中微子等轻子,π、K等介子,Λ等超子,P33等共振态,一系列新的粒子又不断被发现,也不断地刷新人们对于“基本粒子”的认识。尤其是1932年正电子的发现,打开了反物质世界的一扇窗,更激发了人们的兴趣。1950年代之后,反物质世界的大门被打开。当时科学家发现的带电π介子(π+、π-)本身就互为反粒子。195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O.张伯伦与E.塞格雷发现了反质子。次年,在同一实验室的B.柯克等又发现了反中子。待王淦昌等发现 之后,反物质粒子家族的代表性成员就大致齐全了。
之后,反物质粒子家族的代表性成员就大致齐全了。
伴随着基本粒子的大发现,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了各种相应的理论。W.E.泡利的中微子假说与E.费米的β衰变理论为中微子的发现奠定基础(后来R.P.费曼和M.盖尔曼的V-A理论对费米理论进行了修正),H.汤川秀树的介子论的提出则成为μ子和π介子发现的先声。S.坂田昌一针对早期μ为介子的误会提出了2种介子和2种中微子理论。B.卡森与E.U.康登根据核力与电荷无关,提出同位旋的概念及同位旋守恒定律。为解释奇异粒子,A.派斯提出奇异粒子联合产生的理论,M.盖尔曼则提出了奇异量子数,并与西岛和彦提出盖尔曼-西岛法则。对于联合对称,泡利和N.玻尔提出CPT定理,李政道、杨振宁则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而小川修三提出了SU(3)对称性理论。为克服量子场论中微扰理论的困难,J.施温格、S.朝永振一郎与费曼提出重整化理论,盖尔曼则提出了色散关系理论。杨振宁与R.L.米尔斯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在此基础上,J.施温格、S.L.格拉肖开始尝试弱电相互作用统一的规范理论。
用加速器把带电粒子加速到较高能量,是除宇宙线之外,产生高能粒子的主要手段。G.伊辛最早提出直线加速原理,接着R.维德罗意建成第一台直线加速器。T.D.考克饶夫与E.T.S.瓦尔顿建成第一台倍压加速器,M.A.图夫则建成第一台静电加速器。E.O.劳伦斯提出回旋加速器原理,并建成第一台回旋加速器。1940年代中,苏联V.I.维克斯勒和美国E.M.麦克米伦提出自动稳相原理,并由W. H.布洛贝克建成了第一台稳相加速器,这是加速器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1952年E.D.柯隆与M. S.李温斯顿等又提出了强聚焦原理,是为加速器史上的第二次革命。1952年,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成3 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Cosmotron。1954年,位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又建成了能量为6.4 GeV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Bevatron。前述反质子、反中子的发现都是在这台加速器上完成的。
研究微观粒子,首先不可或缺的是探测技术的运用。E.卢瑟福和H.盖革最先制成探测α粒子的气体放电计数管,后来盖革制成可以探测α和β粒子的计数器,盖革与E.W.米勒又发明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盖革-米勒计数管。1912年,C.T.R.威耳逊建成云(雾)室,使带电粒子通过过饱和蒸气,引起气体分子电离,形成小水珠或液滴,从而显示粒子径迹。1932年,P.M.S.布莱克特又发明用计数器控制云室照相。正电子与μ子就是通过云室发现的。1930年代,P.A.切伦科夫发现带电粒子束在透明介质中超光速通过时产生电磁辐射,I.M.弗兰克和I.Y.塔姆对此做了解释,根据这种现象制成了切伦科夫计数器。而反质子、反中子的发现正是通过切伦科夫计数器实现的。1939年,C.F.鲍威尔等开始使用核乳胶探测粒子,后来π-、Λ、Σ、Ξ等粒子都通过核乳胶发现。1952年,D.A.格拉塞发明了气泡室,让带电粒子通过过热液体,引起周围液体汽化,形成气泡,从而显示粒子径迹,与云雾室恰好相反,但更为灵敏。通过这种探测装置,此后科学家发现了一大批共振态粒子。
各类基本粒子的大发现、系列粒子理论的提出、粒子加速与探测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高能粒子物理学科在科学舞台上闪亮登场之初就吸引了大批的学者与研究机构,也为学科进一步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2 1950年代的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基础在国际粒子物理学科从原子核物理中脱胎而出,取得独立形态之际,中国的基本粒子研究因基础薄弱,对于核物理还有着较长时间的依附。
建立于1950年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简称“近代物理所”,1953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再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是新中国亚原子物理的发源地。聚集原本分散于国内外的核与高能物理工作者,开展起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并培养年轻人才,是近代物理所建立之初的最主要工作。10年间,该所从36人激增至4263人[2],其中包括赵忠尧、王淦昌、张文裕、钱三强等实验物理学家,彭桓武、朱洪元等理论物理学家。在他们的带领下,近代物理所在加速器、探测器研制和多个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系列进展。同期,其他单位也有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家建立起粒子物理方面的研究团队,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张宗燧、北京大学的胡宁等。
赵忠尧利用他从美国带回的器材,于1955年建成了在大气中工作的700 keV质子静电加速器V1,后又于1958年建成2.5 MeV质子静电加速器V2及与之配套的重粒子谱仪。通过这2台加速器的研制,中国的加速器技术开始起步,不仅培养了一批加速器人才,还发展了真空、高电压、离子源等技术。以静电加速器为基础,研究所建成了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1955年,谢家麟自美国归国后,开始了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1958年,中国向苏联订购的回旋加速器在房山区坨里原子能新基地建成。
1956年,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改为由苏联、中国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建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此后中国开始筹划本国的高能加速器建设。1957年,由王淦昌领导的7人小组赴苏联学习高能加速器相关科学与技术,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设计了2 GeV电子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后来该方案因“保守落后”,在“大跃进”中搁置。之后赴苏小组在苏联当时建造的质子同步加速器方案基础上,设计了12 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虽然该方案规模较大,但因未能吸收欧美经验,性能较差,后经钱三强等专家研究,再次搁置。1959年底,王淦昌、朱洪元、周光召等建议建造一台中能强流回旋加速器。经力一等赴苏联实习、设计,将能量定为420 MeV。后经论证,该设计方案因对物理意义不大且不易实现,再次搁置[3]。
早在近代物理所成立之初,宇宙线研究即被列为该所4大研究方向之一。1954年,在王淦昌、肖健等领导下,近代物理研究所在云南落雪山海拔3180 m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宇宙线高山实验站。这也是中国第一个高能物理实验基地。赵忠尧、王淦昌分别从美国带回的50 cm×50 cm×25 cm多板云室与直径为30cm的圆云室在宇宙线观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系列云室的建造奠定了基础。1956年,北京又建成30 cm×30 cm×10 cm磁云室,也被安装到落雪实验站。此外,实验站还安装了μ子望远镜与中子记录器,用于观察宇宙线强度的变化。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又决定建一个大型云雾室组。为此,在离原落雪实验室9 km、海拔3222 m处又开始建设新的宇宙线观测站。大云室于1965年安装完毕。
在亚原子物理实验研究中,作为探测器的核乳胶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最初使用的核乳胶为杨澄中、戴传曾从国外带回的英国Ilford公司的C2乳胶,放置过久,灵敏度就会降低,所以自主制造势在必行。何泽慧等从溴化银的乳化工作做起,于1953年做出了灵敏度可与C2相比的乳胶。此后,他们又于1956年研制成功对质子、α粒子、核裂片等灵敏的核-2、核-3乳胶,以及探测慢中子用的核-2载硼、核-2载锂乳胶[4]。1956年,山东大学物理系在王普的带领下,也建立了核乳胶实验室,开展宇宙线研究。另一种探测器卤素计数管和强流管为新型的计数管,充入气体主要为氖和氯或氖和溴。1955年,戴传曾与李德平等研制成功性能优良的卤素盖革计数管,并建立了相应的生产工艺,推广到厂家批量生产。接着,戴传曾小组又研制成功强流管。
利用各种探测装置,留学归国的第一代亚原子物理学家带领大批青年学者,通过加速器实验和宇宙线观测,开展了多个方面的实验研究。如在V1加速器上,研究人员利用自制的核乳胶进行了Li7 (p,α)反应α粒子角分布测量等实验研究;在V2加速器上,研究人员进行了Na23(p,α)Mg24反应等实验研究,并测量了30~200 keV质子轰击Li的反应截面,为核武器设计提供了数据。在回旋加速器上,赵忠尧等进行了质子弹性散射、氘核削裂反应等实验研究工作[5]。落雪实验站还进行了来自宇宙线的K介子和Λ0超子研究[6]。但不可否认,受研究基础与实验装置限制,立足于本土所开展的实验研究水平还很难跟国外同行相比。而受物质条件限制较少的粒子理论研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与个别高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3 王淦昌等的发现王淦昌是清华大学物理系首届毕业生,受教于叶企孙与吴有训。1930年,王淦昌赴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研究所,师从L.迈特纳攻读博士学位。迈特纳后因发现铀裂变而闻名于世,被爱因斯坦称为“我们(德国)的居里夫人”。她从1920年代末开始对放射线连续能谱进行了准确测定。在此基础上,W.E.泡利于1930年提出中微子假说。王淦昌到柏林大学后,开始用β谱仪测量放射性元素β能谱的研究。其测量数据,曾有人说在费米建立β衰变理论时曾有所参考[7]。1930年,W.博特与H.贝克以α粒子轰击Be核,用盖革计数器观察,认为所产生的穿透性极强的射线为γ射线。王淦昌2次提出用云雾室研究此射线的设想,但未获导师迈特纳同意[7]。1931年,约里奥·居里夫妇用电离室观察,发现此射线可从石蜡中打出质子,仍认为是γ射线。1932年,J.查德威克用电离室、计数器、云雾室3种探测器实验,证明该射线是和质子一样重的电中性粒子流,从而发现了中子。
在泡利提出中微子假说之后,为确证中微子的存在,物理学家做了诸多努力,但实验效果却一直不佳。1941年,已是浙江大学教授的王淦昌建议避开普通β衰变过程末态有三体,以至于反冲元素电离效应过小的反应:A→B+e++ν,而选择反应末态只有二体的K电子俘获过程:A+e-→B+ν,测量反冲元素的能量即知中微子的质量[8]。1942年,J.阿伦按王淦昌的建议做Be7的K电子俘获实验,测到了Li7反冲能量,初步证实中微子的存在。后来李炳安、杨振宁专门撰文,强调了王淦昌在中微子发现中的贡献[9]。寻找新粒子是王淦昌多年的目标。在没有加速器的情况下,宇宙线观测是发现高能粒子最可行的方法。1943年,王淦昌提出一种用照相底片寻找宇宙线中粒子径迹的方法[10]。4年后,C.F.鲍威尔利用核乳胶,从宇宙线中发现了π介子。
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简称“联合所”)成立后,中国承担该所经费的20%,每年支付人民币1500~1600万元。自1956年起,中国先后派出王淦昌、胡宁、朱洪元、张文裕、周光召等多批科技人员到联合所工作,首任全权代表是钱三强,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有赵忠尧、王淦昌和胡宁,王淦昌于1959年当选副所长。
王淦昌初到杜布纳之时,自动稳相原理的发现者维克斯勒主持设计的10 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синхрофазотрон)即将(于1957年)建成,能量为世界最高。这一时期正值高能加速器建设的高峰。美国伯克利先后发现反质子、反中子,正是得利于其1954年建成举世无双的6.4 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Bevatron。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8 GeV的PS加速器正在建设中(于1959年完工),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也于同期上马了33 GeV的AGS加速器(1960年建成)。显然,杜布纳的加速器只有短短几年的能量优势。在更高能量的加速器建成之前,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是联合所的王淦昌等高能物理工作者迫在眉睫的事。
王淦昌领导的研究组,最初由2位中国青年学者丁大钊、王祝翔和2位苏联籍青年研究人员及一位苏联籍技术员组成,到1960年发展成由中国、苏联、朝鲜、罗马尼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越南等国20多位研究人员,4位技术员及10余位实验员组成的一个大研究集体(图 1[11])。
 |
图 1 1950年代末王淦昌在杜布纳的研究组 |
王淦昌根据当时研究前沿与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优势,提出2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二是系统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π、Λ0、K0……)产生的规律性。为此,他将工作分成3个小组并列进行,即新粒子研究(由王淦昌负责)、奇异粒子产生特性研究(由丁大钊负责)和π介子多重产生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在轻子、介子、核子的反粒子被一一发现的情况下,寻找超子的反粒子是王淦昌根据加速器的能量优势所做出的一个非常正确的研究方向选择。
在目标确定之后,王淦昌所面临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探测器建设。相比杜布纳的最大加速器而言,当时配套的探测器建设却相形见绌,联合所只有1套确定次级粒子及其飞行方向的闪烁望远镜系统、1台膨胀云雾室和1台大型扩散云雾室,远不能发挥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开展前沿课题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反应系统的选择。让从加速器出来的高能粒子进行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观察次级粒子的产生、飞行、相互作用或衰变的过程,也直接影响实验研究的结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王淦昌选择了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因为反超子寿命极短(10-10s量级),从产生到衰变所能飞行的距离也极短,使用云雾室、气泡室这样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探测器较为适宜。相比而言,气泡室的工作液体本身就是高能反应的靶物质。选择了一类气泡室,靶物质也就随之确定了。为争取时间,王淦昌提出建立一台丙烷气泡室,因其技术上较易实现,且联合所有研制此类气泡室的经验。如要建造质量更好的氢气泡室,就需要花费较为长久的时间,以至于错过加速器的能量优势。虽然利用反质子束打靶更易于产生超子-反超子对,但高纯度的反质子束较难从大量的π-介子和K-介子中分离出来,王淦昌决定用π-介子产生核反应来进行研究[12]。
至1958年春,研究组建成了55 cm×28 cm×14 cm的24 L丙烷气泡室(图 2)。因其尺寸较大,足以同时观察到反超子的产生与衰变[13]。当年秋,研究人员开始用动量为6.8 GeV/c的π-介子与核作用,采集数据;1959年春又用8.3 GeV/c的π-介子开始新的数据采集,前后共收集了近11万张照片,包括数十万个高能π-介子与气泡室工作液体丙烷中的氢和碳核作用事例[14]。
 |
图 2 王淦昌研究组建成的24 L丙烷气泡室(刘金岩2019年4月摄于杜布纳) |
由于反超子衰变的重产物一定是反质子或反中子,湮没星是鉴别其存在的确切标准。王淦昌据此画出了Λ0、 存在的可能图像,要求组内研究人员在扫描照片时注意与图像吻合的事例。1959年3月9日,研究人员终于从扫描的照片中发现了令他们兴奋的事例。如图 3所示,根据对B点出射的6个带电粒子(其中9、11、12、13为质子,8为π+介子,10为π-介子)的测量分析,可以推测为反中子和碳核湮没引发的反应(
存在的可能图像,要求组内研究人员在扫描照片时注意与图像吻合的事例。1959年3月9日,研究人员终于从扫描的照片中发现了令他们兴奋的事例。如图 3所示,根据对B点出射的6个带电粒子(其中9、11、12、13为质子,8为π+介子,10为π-介子)的测量分析,可以推测为反中子和碳核湮没引发的反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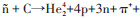 π-+nπ0)。而3为π+介子,由此可推知A点发生的衰变反应:
π-+nπ0)。而3为π+介子,由此可推知A点发生的衰变反应: ,2即为
,2即为 径迹。他们进而推出O点发生的最可能的初级反应为
径迹。他们进而推出O点发生的最可能的初级反应为 +
+ 反冲核[15]。经过计算,观测结果正与预期的一致,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产生”的事例。
反冲核[15]。经过计算,观测结果正与预期的一致,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产生”的事例。
 |
图 3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产生 |
1959年7月,在乌克兰基辅召开的第九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王淦昌小组报告了可能存在 的发现。也就在这次会议上,美国L.W.阿尔瓦雷斯小组展示了一张
的发现。也就在这次会议上,美国L.W.阿尔瓦雷斯小组展示了一张 粒子产生的照片[16]。1960年3月,在确认了
粒子产生的照片[16]。1960年3月,在确认了 的发现之后,王淦昌小组正式将论文投送苏联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ЖЭТФ)与中国《物理学报》发表。
的发现之后,王淦昌小组正式将论文投送苏联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ЖЭТФ)与中国《物理学报》发表。
 是人们发现的第一个带电反超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它证实了此前关于该种反粒子存在的推测,加深了人们对于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17]。当时苏联《自然》杂志称
是人们发现的第一个带电反超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它证实了此前关于该种反粒子存在的推测,加深了人们对于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17]。当时苏联《自然》杂志称 的发现“在微观世界的图像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 [18]。至此,当时人们所知的轻子、介子、核子、超子等组成物质的各类基本粒子都有反粒子被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基本粒子“家族”的一种圆满。1962年3月,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新建成的能量更高(28 GeV)的PS加速器上发现了
的发现“在微观世界的图像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 [18]。至此,当时人们所知的轻子、介子、核子、超子等组成物质的各类基本粒子都有反粒子被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基本粒子“家族”的一种圆满。1962年3月,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新建成的能量更高(28 GeV)的PS加速器上发现了 。该中心在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快报》中指出:“这一发现证明欧洲的物理学家在这一领域内已与美国、苏联并驾齐驱了”。[19]。其意显然相对于反质子和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而言。1972年,杨振宁回国时曾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小组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8]。1982年,王淦昌、丁大钊、王祝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在杜布纳,联合所至今还在建所以来的重要成就中将
。该中心在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快报》中指出:“这一发现证明欧洲的物理学家在这一领域内已与美国、苏联并驾齐驱了”。[19]。其意显然相对于反质子和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而言。1972年,杨振宁回国时曾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小组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8]。1982年,王淦昌、丁大钊、王祝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在杜布纳,联合所至今还在建所以来的重要成就中将 的发现列为第二位[20],并特别将一条路以王淦昌命名(图 4)。
的发现列为第二位[20],并特别将一条路以王淦昌命名(图 4)。
 |
图 4 杜布纳的“王淦昌路”(刘金岩2019年4月摄) |
值得一提的是,王淦昌小组在1959年初还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长寿命、大质量的Д粒子(Д取自俄文“友谊”和“杜布纳”的首字母)。在基辅会议上,由王淦昌做了关于Д粒子迹象的大会报告,而 存在的可能则由丁大钊代表研究组做了报告。二者当时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周光召在报道基辅会议的概况时,用了一大段文字叙述Д粒子,却只用一句话概括了丁大钊的报告,甚至连
存在的可能则由丁大钊代表研究组做了报告。二者当时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周光召在报道基辅会议的概况时,用了一大段文字叙述Д粒子,却只用一句话概括了丁大钊的报告,甚至连 的名字都没有提到[16]。Д粒子的“发现”在高能物理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甚至有美国物理学家“硬说”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粒子[21]。后来经过仔细地讨论分析,该迹象被确定为K+电荷交换现象,Д粒子并不存在[7]。而
的名字都没有提到[16]。Д粒子的“发现”在高能物理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甚至有美国物理学家“硬说”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粒子[21]。后来经过仔细地讨论分析,该迹象被确定为K+电荷交换现象,Д粒子并不存在[7]。而 的发现却最终被确认。
的发现却最终被确认。
当然,种类众多的介子(由正反夸克构成,其反粒子不足为奇)、超子与构成物质的基元——质子、中子、电子的重要性无法相比,更早发现的正电子、反质子与反中子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更为人津津乐道[22-23]。1981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办的《高能物理》杂志封底连载的《基本粒子物理发展史年表》中,1960年的实验成就仅罗列了布鲁克海文AGS加速器的建成和Σ*(1385)共振态的发现2项,1961年的实验成就则罗列了η、ρ、ω、K*等几个介子的发现(图 5[24])。由此可以推测,编者当时并未认为发现 的重要性与这些粒子的发现相当,故未将之列入。该杂志编辑部后将此连载的年表汇集成书,并于1985年出版。书中罗列的1960年实验成就则多出了一项
的重要性与这些粒子的发现相当,故未将之列入。该杂志编辑部后将此连载的年表汇集成书,并于1985年出版。书中罗列的1960年实验成就则多出了一项 的发现,且名列榜首(图 6)[25]。这可能与王淦昌等已于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有关。
的发现,且名列榜首(图 6)[25]。这可能与王淦昌等已于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有关。
 |
图 5 《高能物理》杂志连载的《基本粒子物理发展史年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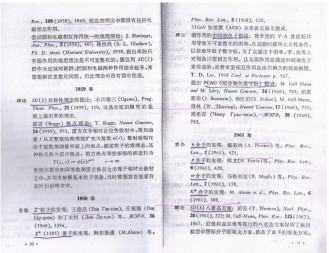 |
图 6 汇集成书的《基本粒子物理发展史年表》中的一页 |
王淦昌等 的发现,乃至其他中国学者在杜布纳所做的科学研究,科学意义倒在其次;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工作打开了中外科学交流的窗口,让中国学者接触到了科学的最前沿,大开了眼界。正如周光召所说,他觉得在联合所“更接近世界最新科学的前线”,可以“迅速吸收世界核子科学研究的成果” [26]。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在一份关于高能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的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任务,高能原子核实验物理要利用联合所的条件培养一定数量的干部;在1962年之前完成实验技术的准备;利用联合所加速器提供的材料,在国内组织高能研究队伍。而在基本粒子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以利用联合所条件培养干部、组织队伍为先[27]。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利用联合所培养人才。事实上后来也确实达到了培养、锻炼研究人员的目的。
的发现,乃至其他中国学者在杜布纳所做的科学研究,科学意义倒在其次;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工作打开了中外科学交流的窗口,让中国学者接触到了科学的最前沿,大开了眼界。正如周光召所说,他觉得在联合所“更接近世界最新科学的前线”,可以“迅速吸收世界核子科学研究的成果” [26]。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在一份关于高能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的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任务,高能原子核实验物理要利用联合所的条件培养一定数量的干部;在1962年之前完成实验技术的准备;利用联合所加速器提供的材料,在国内组织高能研究队伍。而在基本粒子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以利用联合所条件培养干部、组织队伍为先[27]。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利用联合所培养人才。事实上后来也确实达到了培养、锻炼研究人员的目的。
除 的发现之外,王淦昌小组通过π介子与核子相互作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1]。1960年底,王淦昌回国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1961年接替王淦昌任联合所中国组组长的张文裕领导联合研究组,使用王淦昌等研制的24 L丙烷气泡室,在10 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开展了共振态的研究,并得到了一些填补空白的重要结果。唐孝威、吕敏等一些年轻的实验工作者也做出了一些出色的工作。而中国学者在杜布纳的理论研究,以周光召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赝矢量流守恒律的观念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为弱相互作用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进,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国外人士称赞“周光召的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28-29]。胡宁在色散关系理论、基本粒子的分类方面,朱洪元在利用色散关系对π介子之间及π介子与核子之间的低能强相互作用方面,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获得了重要的结果。
的发现之外,王淦昌小组通过π介子与核子相互作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1]。1960年底,王淦昌回国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1961年接替王淦昌任联合所中国组组长的张文裕领导联合研究组,使用王淦昌等研制的24 L丙烷气泡室,在10 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开展了共振态的研究,并得到了一些填补空白的重要结果。唐孝威、吕敏等一些年轻的实验工作者也做出了一些出色的工作。而中国学者在杜布纳的理论研究,以周光召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赝矢量流守恒律的观念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为弱相互作用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进,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国外人士称赞“周光召的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28-29]。胡宁在色散关系理论、基本粒子的分类方面,朱洪元在利用色散关系对π介子之间及π介子与核子之间的低能强相互作用方面,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获得了重要的结果。
在本土加速器研制方面,无论是1958年的2 GeV电子同步加速器方案、1959年的12 GeV质子同步加速器方案、1960年的420 MeV中能强流回旋加速器方案,都是王淦昌等在苏联完成,或借鉴了苏联的方案。而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高能加速器建设,包括1965年提出的6 GeV质子同步加速器方案、1969年的1 GeV质子直线加速器方案,也都是以赴苏科技人员为主力而提出[3]。
在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尤其在“文革”前的10年内,在中国从事核与粒子物理研究的主力军中,除赵忠尧等自欧美留学归来的第一代亚原子物理学家之外,赴苏科学家构成了重要的班底。周光召、丁大钊、王祝翔、何祚庥、吕敏、方守贤、王乃彦、钱绍钧、冼鼎昌、王世绩等后来都成为中国亚原子物理研究的骨干力量。在退出杜布纳之后,中国就开始计划在本土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在一份建议书中特别提到:“几年来,先后到联合所工作的有140余人,参加过有关学术会议的有200余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力量[30]。可以说,王淦昌等中国学者在杜布纳联合所的科学工作,为此后中国本土高能粒子物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与人才基础。还有很多从杜布纳回国的青年学者,参与了核武器研制,默默无闻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不再赘述。
| [1] | Weinberg S. The Discovery of subatomic particles[M]. Cambridge: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3: 9. |
| [2] | 葛能全. 钱三强年谱长编[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176, 323. |
| [3] | 丁兆君, 胡化凯. “七下八上”的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J]. 科学文化评论, 2006, 3(2): 85-104. |
| [4] | 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得奖科学研究论著评审意见[J]. 科学通报, 1957(增刊1): 5-19. |
| [5] | 赵忠尧. 我的回忆[J]. 现代物理知识, 1993(2): 43-44. |
| [6] | 霍安祥. 宇宙线研究三十年[J]. 高能物理, 1979(3): 8-9. |
| [7] | 王淦昌. 无尽的追问[M].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
| [8] | Kan Chang Wang. A suggestion on the detection of the neutrino[J]. Physical Review, 1942(61): 97. |
| [9] | 李炳安, 杨振宁. 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6(5): 34-39. |
| [10] | Wang K C. A suggestion on a new experimental method for cosmic-ray particles[J]. Science Record, 1945(1): 387. |
| [11] | 王乃彦. 王淦昌全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 [12] |
丁大钊. 反西格马负超子( )的发现——记王淦昌教授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M]//胡济民, 许良英, 汪容, 等.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7: 77-89. )的发现——记王淦昌教授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M]//胡济民, 许良英, 汪容, 等.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7: 77-89.
|
| [13] |
王祝翔. 王淦昌的实验工作之一——反西格马负超子( )的发现[M]//胡济民, 许良英, 汪容, 等.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7: 141-144. )的发现[M]//胡济民, 许良英, 汪容, 等.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7: 141-144.
|
| [14] | 丁大钊. 无尽的探索——丁大钊传[M].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33-34. |
| [15] |
王淦昌, 王祝翔, 维克斯勒, 等. 8.3Бев/c的负π介子所产生的 超子[J]. 物理学报, 1960, 16(7): 365. 超子[J]. 物理学报, 1960, 16(7): 365.
|
| [16] | 周光召. 基辅高能物理会议的概况[J]. 原子能科学技术, 1959(3): 185-187. |
| [17] | 人类对基本粒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王淦昌在京谈“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的重大意义[N]. 人民日报, 1960-03-28(5). |
| [18] | 范岱年, 亓方. 王淦昌先生传略[M]//胡济民, 许良英, 汪容, 等.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7: 224-268. |
| [19] | New fundamental particle discovered, the ANTI-XI-MI-NUS[J]. CERN Courier, 1962, 2(3): 4-5. |
| [20] | 王寿群. 以身许国――那些从杜布纳回国的科学家的故事[M]. 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17: 16. |
| [21] | 对于理解基本粒子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中苏等国科学家发现新基本粒子发现新粒子使用的探测器是中国科学家设计的[N]. 人民日报, 1960-03-26(5). |
| [22] | 埃米里奥·赛格雷. 从X射线到夸克――近代物理学家和他们的发现[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4: 285-286. |
| [23] | 斯蒂芬·温伯格. 亚原子粒子的发现[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95-199. |
| [24] | 《高能物理》编辑部. 基本粒子物理发展史年表[J]. 高能物理, 1981(3):封四. |
| [25] | 《高能物理》编辑部. 基本粒子物理发展史年表[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32-33. |
| [26] | 在世界最新科学的前线——联合核子研究所中苏科学家互助合作进行研究布洛欣泽夫、王淦昌都说希望中国派去更多研究人员[N]. 人民日报, 1957-04-18(5). |
| [27] | 高能原子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五年计划的任务和指标: 1958-10[B]. 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档案室(A006-00051-003-58.10-3). |
| [28] | 戴明华, 张杉, 李云玲. 周光召[M]//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4: 187-196. |
| [29] | 吴岳良, 刘金岩. 周光召对理论物理和原子能事业的贡献[J]. 物理, 2019, 48(5): 295-300. |
| [30] | 关于建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建议: 1965-6-26[B]. 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档案室(A006-00125-007-73.03.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