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图 1)的第一卷《导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多卷本的著作,上迄中国上古时期,下至明清之交欧洲传教士来华,涉及科学思想史、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众多中国科技门类,又加之是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可谓是史无前例,故而《导论》卷甫一出版便引发了海内外学界的瞩目和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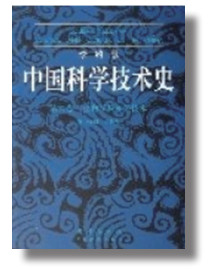 |
图 1 《中国科学技术史》书影 |
华裔汉学家杨联陞(1914—1990年),除治中国经济史外,还曾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书评,涉及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地理、科技史等众多领域,是当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尝自称“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其实正如其所言“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1]。颇为有影响的包括杨联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的系列书评,其中便论及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并且在其他场合,也多次提及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1 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肯定与价值评判在书评开篇,杨联陞便指出李约瑟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历史跨度大、覆盖领域广,撰写如此规模的一部通史对著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智力挑战。但是杨联陞认为,李约瑟具备了很好的条件来接受这一挑战,具备了写作这样一部通史所需的学术资质和条件。科学素养:对欧洲科学史有广泛的认知,对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实地调研:在中国生活游历过;文献功夫:懂得中文,可以查阅原始文献;中国助手的帮助:比如王铃博士,其他中国学者的协助。
在这些主客观条件基础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杨联陞看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价值在于2个方面:1)指出尽管有偏于人文主义的主导倾向,中国文明确实取得了可观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人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方面,中国曾有过巨大的贡献;2)试图确定这些科学技术成就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贡献的大小和意义。颇为重要的是,杨联陞在此提及了李约瑟于1946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开幕式的一次讲演,对于解答“李约瑟之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中国文明中,哪些限制性因素致使16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现代科学与工业革命?在演讲中,李约瑟强调的是某些具体的物质因素,但同时承认理念也很重要,他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与欧洲的游牧文明不同,基本上是一种灌溉农业的文明,从而使得商人阶层无法执政。有能力的人随处皆是,却没有有利的条件。
2 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错误在肯定李约瑟研究成果的同时,杨联陞客观而诚恳地指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存在的若干失误,这包括文献使用、文字训诂、历史地理知识、拼读与翻译等方面。
在文献征引方面的错误。杨联陞本人自称是“开汉学杂货铺的”,言外之意是其知识面非常广泛,而且其学术视野也是全球性的。他在评《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便指出李约瑟对日文文献的遗漏。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文明方面是非常活跃的,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方面,出版了很多重要的书籍和论文,所以“遗漏日文文献确实不走运”;而且杨联陞还指出,本卷内容李约瑟主要依据的是西方语言所做的研究,在1985年致中国学者杜维运的一封信札中,杨联陞指出“大著称Needham为汉学家,欠妥。译其书为科学艺术史,艺术应为技术,Needham自己书亦如此作。他自己中文有限”[2]。如此,必然导致李约瑟在文字训诂、历史地理知识、拼读与翻译等方面出现失误。
杨联陞举出了几条例证,证明李约瑟在文字训诂方面是相当粗疏的。比如在序言中,李约瑟提及公元前4世纪《墨子》中关于纺织技术的一段话,其中出现了“刻镂”一词。李约瑟认为该词的字面意思是“切割和雕刻”(cut and engraved),无疑指的是“刻丝”。对此,杨联陞指出,李约瑟认为“刻镂”是“切割和雕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词只是对固体材料而言,而不能用于纺织品。将“刻镂”等同于“刻丝”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为刻丝技术或丝织锦缎仅从宋朝开始才在中国兴盛起来;此外,在论及古代掘井取水技术时,《中国科学技术史》涉及《史记》中的“秦人”助力大宛人掘井取水的史料,其中对于“秦人”是汉人、叙利亚人还是希腊人,李约瑟无法给出定论。杨联陞结合李约瑟不曾得知的伯希和的(Paul Pelliot,1878—1945)《“支那”名称之起源》与王国维的《西域井渠考》等相关研究,指出“秦人”指的就是汉人;而且指出,开掘深井的技术是从中国本土传到西域去的。
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历史地理知识方面的纰漏,杨联陞也一一加以指出。比如书中关于中国南北朝的一段描述,其中说“the last of these,the Liang”,显然“梁”不是南朝的最后一个,而是倒数第二个王朝;再比如说杨坚“He ruthlessly destroy the Liang in 587 and overcame the Chhen and the Chhi in north two years later”,对此,杨联陞指出,在公元587年被摧毁的梁是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另一个“梁”,在历史上称为后梁。南方的陈,于公元589年被隋征服。北方的齐,是在557年被北周征服的。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谓陈和齐都出现在北方,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另外,关于鸵鸟这一动物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李约瑟认为鸵鸟、斑马、长颈鹿之类动物初次出现在明朝;但是杨联陞却认为这一判断是错的,他指出,据班固的《西都赋》和《汉书》,在汉代的皇家花园中便豢养有进贡的鸵鸟;另外,汉学家劳费尔(Berhold Laufer,1874—1934)在其《美索不达米亚的鸵鸟蛋壳杯以及古代和现代的鸵鸟》(Ostrich Egg-shell Cup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Ostrich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一书中指出,在公元101年,鸵鸟的活标本和狮子便由波斯运抵了中国;公元650年的唐朝时期,吐火罗国又曾送给中国鸵鸟。在汉代,鸵鸟被称为“大雀”,在唐代,则被称为“鸵鸟”。
在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河南境内的“洛河”写的是“Lo Chiang”(洛江),而陕西西部的“洛河”则写成了“Lo ho”(洛河)。杨联陞指出,实际上两者都叫作洛河或洛水,后者有时也叫做“北洛水”。另外,周代封建诸侯国,比如邾国和邹国,是在泗水流域,而不是在淮河流域;邓国是在汉水流域,而不是在泗水流域。
在拼读和翻译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如秦始皇曾派徐巿(福)远赴东瀛,因为汉字“巿”与“市”形似,所以杨联陞指出,李约瑟误将“Hsü Fu”拼作了“Hsü Shih”;再如沈括所著的《忘怀录》书名,李约瑟将之译为“What not to Forget to take with you(when Preparing for a Journey)”(“旅行时”不应忘带之物品),对此杨联陞指出,“忘怀”通常指的是不计得失,也就是不计较世俗之得失,从而轻松自由。杨联陞建议,《忘怀录》书名可以译作“Notes of a Free Mind”。在笔者看来,李约瑟的译法似乎是意译,因为书中确实也包括了一份旅途需要携带的物品清单,并且也讲到了如何制作马车、摇椅、折叠床、观赏雪景用的可移动屏风,以及无需他人服侍的温酒铜器等,皆为旅途所必备之物。
3 杨联陞与李约瑟的其他往事当然,杨联陞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评论,是二人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杨联陞与李约瑟也有其他一些往来,主要也都是学术方面的。在1940—1950年,杨联陞曾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欧洲访学,在剑桥受到了李约瑟的热情接待,不但阅读了李约瑟的藏书,而且二人相谈甚欢。据说当时二人谈到《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的“蒸土筑墙,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一句,李约瑟兴致勃发,立即找到原文,要杨联陞口译,他随即打字记下。而后,二人保持着学术上的密切联系,杨联陞在评日本汉学家薮内清的《中国的天文学》时曾提及李约瑟,内容是李约瑟曾告诉他,加州大学的陈世骧教授提醒其关注敦煌手抄文书第3326号里面的中国星图,而李约瑟也准备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讨论这些敦煌星图。时隔近30年后,1984年杨联陞在台湾讲学时,还记得《中国科学技术史》书评一事,后来李约瑟等的著作第一卷出版,杨联陞在书评中指出了若干错误,再见面时就有些冷落了。引用另一位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的话,李约瑟此册中有许多错误(many mistakes),但是杨联陞很诚恳地表明“我对于李约瑟的巨著还是十分敬佩的!”“他们做的是开荒性的工作,一年不知要看要译多少书,岂能毫无失误!”。
杨联陞在其日记中曾写道“说与邻翁浑不解,通人本职是沟通”[3],他是心怀恕道的,杨联陞在汉学界自称是做“沟通”工作,其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评论“以改正此等错误为主,但不用伤人字句”,不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那般自称汉学界之警犬,对于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不留情面。杨联陞以君子之风和渊博的学识,写就的精细而公允的学术书评,为我们重新审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份文献资料。面对西方汉学家,杨联陞所展现出的学术自信与质疑精神,对于我们今日的海外汉学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 [1] | 杨联陞. 汉学书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458. |
| [2] | 杨联陞. 莲生书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457. |
| [3] | 蒋力. 杨联陞别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