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12 月,中国青年学者邢立达与加拿大学者McKellar 等在国际著名期刊《当代生物学》上报道了一块发现于缅甸克钦邦胡康河谷的白垩纪中期距今约9900 万年的琥珀,这块拇指大小的琥珀保存了一段尾巴,尾巴上有序地丛生着有明显羽干和羽枝分化的羽毛,它的保存状态非常好,极为精细的羽毛结构都得以完美保存[1]。令人诧异的是,经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徐星鉴定,这段长羽毛的尾巴并不属于鸟类,而是属于一种小型的虚骨龙类恐龙。文章的另一位共同第一作者黎刚利用同步辐射X 光相衬CT扫描、荧光成像和吸收谱分析,不仅三维重建了这段尾巴的形态,而且还探测出二价铁元素,表明可能曾经存在血红蛋白和铁蛋白。高度精细的结构以及可能存在的软组织遗存,给人极具诱惑的暗示,让人似乎感到儿时复活恐龙的梦想可能就要实现了。2016 年6 月,邢立达和McKellar 等[2]还曾在《自然-通讯》上报道了两枚同样是产自于缅甸克钦邦的琥珀,令人称奇的是这两块琥珀各自包裹了一个非常小的雏鸟的翅膀,两个翅膀都原位保存了骨骼、羽毛甚至一些被作者们称为软组织的结构。这两只翅膀虽然不能让人联想起复活恐龙,但是就其科学意义而言,却与那枚恐龙尾巴有着密切的关系。
1 琥珀中的动物世界琥珀是树脂形成的化石,因其特殊的质地与美丽的色彩而被视为珍宝。琥珀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都有记述,在中国的典籍中更有“松脂入地所化”的说法,称汉时西域诸国中的罽宾国产琥珀。琥珀不同于其他种类的化石,其中常常有包裹体。这些包裹体可以是非生物成分,也可以是生物成分,是树脂在石化之前包裹的物质。包裹在琥珀中的生物成分有细菌、藻类、真菌、高等植物、节肢动物、甚至是脊椎动物等。包裹有动物的琥珀在中国收藏者中被统称为“虫珀”。树脂埋藏于地层中逐渐石化并变成琥珀的过程被称为琥珀化(amberiza⁃tion),琥珀化的过程缓慢而轻柔,对于保存昆虫等细小和柔韧的生物体非常有利,因此保存于琥珀中的化石往往是同类化石中最为完整和精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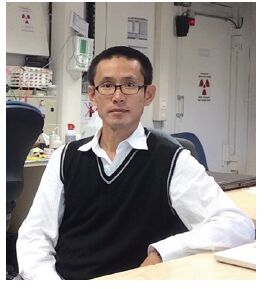
琥珀中包裹的的动物以昆虫和蛛形纲等节肢动物最为常见,而对于琥珀中节肢动物的研究已经有200 多年的历史。已经发现的琥珀中的节肢动物多样性非常高,十余年前曾有人统计,仅在多米尼加的新生代琥珀中就发现了多达235 个科的昆虫。近10 年来,研究琥珀中节肢动物的学者大幅增加,研究地点也扩展到缅甸、印度、中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新发表的琥珀中保存的节肢动物化石种类和数量也大幅增加,例如德国Rust 等研究的产自印度古吉拉特早始新世琥珀中的节肢动物,其多样性就高达55 科100 种以上。这些节肢动物不仅保存了很多化石种类的精细形态学特征,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动物地理学意义,表明印度次大陆在早始新世就已经摆脱了动物地理隔离状态。
绝大多数的包裹有节肢动物的琥珀发现于白垩纪和新生代地层,2012 年,Schmidt 等[3]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报道的发现于意大利东北部晚三叠纪地层的、距今约23000 万年的1 种蝇和2 种螨,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包裹于琥珀的节肢动物。包裹有脊椎动物的琥珀非常稀少,但是在脊椎动物各大门类中,除鱼类尚未发现有包裹于琥珀的纪录之外,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都曾出现于琥珀包埋体中。我国琥珀收藏者夏方远等人与青年学者史恭乐、王博根据私人藏品出版的科普读物《琥珀》一书,不仅纪录了大量保存精美的植物和节肢动物,还有蜥蜴、蛙、鸟类的羽毛等。
目前已知,保存于琥珀中的两栖类化石纪录寥寥无几,美国学者Poinar 和Cannatella 于1987 年在《科学》上报到了首个保存于琥珀中的两栖类化石[4]。这块琥珀发现于多米尼加的晚始新世地层,距今约3500 万~4000 万年。其中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无尾两栖类和另外一个个体的3 条腿。较为完整的个体的部分皮肤和眼睛保存完好,但是身体的大部分已经变得透明,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骨骼系统。这两个包裹于琥珀的两栖类化石属于细趾蟾科的一种卵齿蟾(Eleutherodactylus),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种雨蛙。
相较于其他脊椎动物而言,琥珀中出现的蜥蜴类包裹体是相对丰富的。例如,Sherratt 等[5]于2015 年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的文章,一次就报道了17个包裹于琥珀中的安乐蜥类化石,这些含蜥蜴的琥珀都产自于多米尼加距今约1700 万~2000 万年的中新世地层。Sherratt 等采用目前流行的高精度X 光CT 扫描技术,数字化地重建了这些琥珀中蜥蜴从皮肤到骨骼的精细三维结构,详细地研究了这些蜥蜴的生态型,通过统计分析和对比,发现这些化石蜥蜴代表了4 个生态型,与现生安乐蜥的生态型非常相近,由此证明现代加勒比地区安乐蜥的生态类型早在中新世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再如,Daza 等[6]于刚刚过去的2016 年在《科学进展》上报道了产自缅甸白垩纪中期的包裹于琥珀的12 种蜥蜴类化石,这些含蜥蜴的琥珀与含恐龙尾巴的琥珀出自同一地区,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保存于琥珀之中的蜥蜴类动物群。这些琥珀很多都非常好地保存了软组织和骨骼系统,研究者们同样利用高精度X 光CT 扫描技术,详细比较了这些琥珀中的蜥蜴类化石与其他化石和现生蜥蜴类的差别,发现这些化石包括了基干有鳞类、壁虎亚目、蜥蜴亚目和变色龙类4 个大的类群。这一发现表明高度多样的旧大陆热带蜥蜴类组合早在白垩纪中期就已经形成了,在经历了白垩纪-古近纪之交的恐龙灭绝事件之后,这一蜥蜴类组合在现生群中仍表现出遗传连续性。
琥珀中包裹有哺乳动物的纪录非常稀少,除了时有发现的一点含有哺乳动物毛发的琥珀之外,含有哺乳动物身体的琥珀纪录几乎为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MacPhee 和Grimaldi 于1996年在《自然》上首次报道了一块包裹有哺乳动物骨骼的琥珀[7]。这块不足2 cm 的琥珀同样也发现于多米尼加,距今约1800 万~2900 万年。其中保存的并不是完整的个体,而是仅包裹了6 枚胸部椎体和与这些胸椎相关节的部分肋骨。根据这些骨头的形态,MacPhee 和Grimaldi判定这个哺乳动物是与现生沟齿鼩相似的一种食虫类动物。
鸟类和恐龙出现于琥珀之中,并不比哺乳动物更为稀少,但是所能见到的并不是完整的身体,甚至称不上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仅仅是零散的羽毛。像邢立达等所报道的包裹有鸟类翅膀和恐龙尾巴的琥珀,确实是非常稀有的。
2 羽毛与恐龙化鸟无论是恐龙尾巴,还是鸟的翅膀,这两项发现的科学意义首先在于它们完整地原位保存了羽毛。羽毛是非常复杂的结构,提起羽毛,人们首先就会想到鸟类。经典动物学教材通常会指出,羽毛是鸟类起源与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结构,是鸟类特有的皮肤衍生物。羽毛的演化与发生过程则是经典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发育生物学等领域时常关注的问题。那么,鸟类的羽毛怎么会长到恐龙尾巴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近年来由中国学者引领的关于鸟类和恐龙演化关系的研究,正是鸟类和恐龙的羽毛,在恐龙和鸟类这两大类群之间架起了一座演化发育的桥梁。
关于鸟类与恐龙之间演化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1868年,Huxley 就提出,一种名为美颌龙的恐龙是介于其他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动物,稍后,他又将美颌龙描绘成一种有羽毛的动物。1926年,丹麦艺术家兼业余动物学家Gerhard Heilmann 以英文发表了《鸟类起源》一书,详细阐述了鸟类与包括美颌龙在内的其他恐龙的形态差异,重新提出鸟类起源于假鳄类的假说。这本书影响深远,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虽有Ostrom[8]于1976 在《林奈学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长文、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一些试图证明虚骨龙类恐龙与鸟类的亲缘关系更近的研究,但是鸟类起源于假鳄类的学说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1996年,中国学者季强与姬书安在《中国地质》期刊上上命名了原始中华龙鸟(Sinosauropteryx prima)化石,并提出该化石保存有原始羽毛,由此开启了一个鸟类与恐龙演化关系研究的新时代。中华龙鸟化石发现于辽宁省北票市四合屯早白垩纪地层,距今约12200 万~12460 万年,虽然最初被鉴定为一种原始的鸟类,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它是一种与德国晚侏罗纪的美颌龙非常相似的虚骨龙类恐龙。中华龙鸟化石的背部和尾巴保存有厚密的纤羽状皮肤衍生物的印痕,季强和姬书安认为这些印痕是未分化的原始羽毛,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论,现在已经逐渐被多数学者所接受,恐龙专家徐星最近在总结鸟类与恐龙演化关系时,已经把中华龙鸟列入具有羽毛的恐龙之列。自中华龙鸟之后,在中国已经发现了大量的保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其中一些恐龙不仅有发育良好的羽毛,甚至形成鸟类一样的翅膀,比如一种被称为小盗龙的恐龙,其前肢和后肢都发育有翅膀状结构。
在中国发现的这些带羽毛的恐龙和鸟类,虽然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恐龙与鸟类羽毛的高度相似性,但毕竟所这些标本中的羽毛都是压扁的、是以印痕为主的化石。琥珀中羽毛化石的发现,让人们得以一窥远古羽毛的真实形态。
保存于琥珀中的羽毛并不十分罕见,但是在中国发现鸟类和恐龙羽毛印痕之前,研究者对琥珀中的羽毛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而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2011年,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McKellar 等[9]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研究了在加拿大草湖地区晚白垩纪富煤地层的琥珀,从4000 多枚标本中发现了11 枚含有羽毛包裹体的琥珀。这些羽毛既有纤羽状的属于非鸟恐龙的原羽毛,也有含有色素沉积的适应于飞行或潜水的进步鸟羽。美国学者Prum[10] 曾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羽毛的演化与发育起源”的论文。这篇论文在综述鸟类羽毛形态类型和发育过程的基础上,详细解读了当时已知的中华龙鸟和北票龙的纤维状皮肤附属物与进步羽毛的关系,进而把鸟类羽毛演化发育的过程分为5 个阶段。Ryan C. McKellar 等的研究发现,加拿大琥珀中保存的恐龙与鸟类羽毛的多种形态恰好可以与这5 个阶段相对应。
邢立达和McKellar 等近期在《当代生物学》上报道的包裹于琥珀之中的恐龙尾巴,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其羽毛的立体形态,再次证明,虚骨龙类恐龙不仅有着与鸟类一样复杂的羽毛,而且还有着与鸟类相似的羽毛排列模式。
邢立达和McKellar 等最近在《自然-通讯》上报道的包裹于琥珀之中的雏鸟翅膀原位保存了骨骼和羽毛。文章的共同作者黎刚,利用同步辐射X 光相衬成像技术,复原了两件标本的骨骼、羽轴、皮肤、肌肉等特征,详细的研究表明两个翅膀可能来自于同一个物种,属于已经灭绝了的、被称为“反鸟”的鸟类。反鸟是恐龙时代种类最多样、化石数量最丰富的鸟类,是鸟类演化历史中一个很大的支系。在中生代之后,反鸟随着恐龙时代的结束而灭绝了。多数反鸟的嘴里长有牙齿,翅膀保留有爪,肩部关节的形态恰好与现代鸟类相反,除此之外,反鸟的外部形态与现代鸟类并没有太多差别。邢立达和McKellar 等认为,缅甸琥珀中的这两个非常微小的翅膀属于早成鸟的翅膀,也就是说它们在刚刚孵化之时已经发育得很好,不久就能够四处活动和取食了。从这两个翅膀羽毛的排列方式来看,与现生鸟类非常相似。
Navalón 等[11]来自于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学者2015年在《科学报告》上发表了发现于西班牙早白垩纪的一段保存有羽毛、肌肉和结题组织印痕的反鸟类翅膀化石,这块化石显示小肌肉、肌腱、韧带连接于飞羽的滤泡,进而形成一个在飞行中维持翅膀整体形态和功能整体的系统,这样的模式与现生鸟类的翅膀近乎相同。琥珀中鸟类翅膀的发现,印证了Navalón 等的发现,再次证明鸟类具有的完美适应于飞行活动的羽衣模式和翅膀结构早在中生代就已经形成。
包裹于琥珀中的羽毛,不管是恐龙的还是鸟类的,都为人们提供了非常精细的形态学信息,使得人们对恐龙化鸟的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目前已知的早期化石鸟类和鸟类的近亲虚骨龙类恐龙,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动物,两者各自具有形态多样且功能完备的羽毛和羽衣。近20 多年来发现的大量而多样性极高的早白垩纪鸟类与虚骨龙类化石表明,两类动物可能在侏罗纪末期就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多样性辐射。在更早一些时候的侏罗纪中后期,鸟类与其恐龙近亲的相似程度如此之高,有时到了难以分辨的程度。生活在距今大约15000万年~16500 万年前的始祖鸟,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最早的鸟类,但也有学者认为始祖鸟是一种兽脚类恐龙。差不多同时期的与鸟类亲缘关系很近的兽脚类恐龙近鸟龙和晓廷龙,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其实就是鸟类。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近鸟龙和晓廷龙都有真正的羽毛。始祖鸟、近鸟龙和晓廷龙如此相近,表明它们才刚分开不久,但是它们毕竟还都是同时代的动物,它们的共同祖先显然应该存在于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如果要给恐龙化鸟的开始时间一个合理的估计,我认为是在早侏罗纪,距今大约2 亿年的时候。至于原始羽毛的出现,自然比鸟类和兽脚类恐龙共同祖先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应该是三叠纪的某一个时期。
3 从古DNA到侏罗纪公园琥珀中的鸟翅膀和恐龙尾巴,为研究羽毛的演化发育与恐龙化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证据,但对于不关心研究细节的人来说,不过是“一地鸡毛”。人们似乎看到那根乱草一样的尾巴中还保存着鲜红的血液并闪着企盼的目光,迫切地想知道科学家们什么时候可以复活一只恐龙。
早在1993年,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已经告诉我们该如何克隆一只恐龙了,过程是这样的:找一只包裹于琥珀的蚊子,取出其腹部的一滴血,然后从这一滴血克隆恐龙的DNA,有了恐龙DNA 就可以复活恐龙了。Borkent 和Grimaldi[12]曾于2004年报道了包裹于缅甸琥珀中的中生代蚊子化石,据称这是最早的蚊子化石,而且从该化石的触角和口器来看,有可能是吸食脊椎动物血液的。看来试验材料似乎不是问题,试验流程也看似合理,而12年过去了,电影还是电影,恐龙还只是模型,花了纳税人不少钱的科学家们都在干什么?现在木乃伊化的恐龙尾巴也发现了,我们距离复活恐龙应该是更进一步了吧?
从死亡的生物体残存物或其生存环境中提取到的、已经部分降解的DNA 被称为“古DNA”。要想克隆恐龙DNA 或者复活恐龙,我们首先应该先了解一下古DNA 相关研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早在1984年,美国的Higuchi 等[13]便从博物馆干肌肉标本中提取到了已经灭绝100 多年的南非斑驴的DNA。稍后,瑞典籍学者Pääbo 陆续发表了从4000 多年的木乃伊中、7000年的脑组织中甚至是13000年的地獭皮中提取到DNA[14]。再随后,美国的Goldenberg 等[15]于1990年在《自然》上发表了文章,宣称从美国著名化石地点Clarkia 的距今1700 万~2000 万年的中新世植物化石中提取到了DNA。这篇文章大大激发了研究者的想象力,又过了两年,美国的DeSalle 等[16]在《科学》上发文声称,在距今约2500 万~3000 万年的琥珀中克隆了一种化石白蚁的DNA。紧随其后,美国的Cano 等[17]于1993年在《自然》上发文称从一块来自于黎巴嫩的距今约12000 万~13500万年的琥珀中克隆了一种化石象鼻虫的DNA。1994年,美国的Woodward 等[18]终于在《科学》上发表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恐龙DNA”,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发表的距今约8000 万年的“恐龙DNA”,竟然是从犹他州的一处煤矿坑道的顶棚中发现的恐龙骨片中提取的。再过一年,来自于北京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连续发文,声称在一枚破损的恐龙蛋中也提取到了DNA。
在古DNA 克隆工作方兴未艾、很多珍贵的博物馆标本面临即将被破坏之时,一些冷静的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起。西班牙学者Gutiérrez 和Marín[19]于1998年在《分子生物学与演化》上撰文指出,包括Cano 等的研究在内,大多数的从琥珀中提取的所谓的古DNA 实际上都来自于现代污染物。随后大量研究都表明,很多在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古DNA,包括广受关注的恐龙DNA,不是不能被重复,就是明显来自于现代生物的污染。2012年,丹麦的Allentoft 和澳大利亚的Bunce 领导的国际团队研究了3 种新西兰恐鸟的158 块标本,通过比较这些标本的年代和残存DNA 量,他们发现DNA 这种大分子物质有一个521年的“半衰期”,即使是在假定的-5℃的保存状态下,DNA 完全降解的时间也仅有680 万年。实际上,从现在回溯这样长时间的持续低温的环境,在地球上几乎是不存在的。Allentoft 和Bunce 等的研究发表在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20],这项研究不仅表明以往发表的很多古老的DNA 可能都来自于污染物,而且也等于宣布复活恐龙是不可能的。
从百万年以上的化石中提取古DNA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另一方面,从相对年轻的化石中克隆DNA 的相关研究则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二代测序技术(NGS 技术)逐渐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以后。一些新近的研究已经不是提取少量DNA 片段那么简单,而是在基因组水平上的全核基因克隆。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是关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基因组及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基因交流方面的一系列研究。
近年来,在古DNA 的阴影中一种被称为古蛋白分析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所谓古蛋白是指在生物体遗存或者化石中保存的蛋白质。蛋白质比起DNA 来说要稳定得多,特别是组成皮肤衍生物的角蛋白及肌腱、韧带、骨骼等结缔组织中的胶原蛋白,是非常稳定的大分子有机物。1994年,美国学者Schweitzer 等就提出,恐龙骨骼中可以保存胶原蛋白。其后,她又利用免疫学方法从距今约7000 万~7500 万年的恐龙和鸟类化石中检测到了角蛋白。2015年,英国学者Welker[21]领导的国际团队从已经灭绝的南美有蹄类动物箭齿兽和后弓兽的骨骼化石中提取到了胶原蛋白,并以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为基础构建了这两种绝灭动物与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系统关系,结果显示箭齿兽和后弓兽与现生奇蹄类动物的亲缘关系非常近。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了《自然》上,它不仅为解决南美有蹄类起源这个自达尔文以来的百年谜题提供了新线索,也开启了一个把蛋白组学应用于古生物学研究的先河。最近,中国青年学者泮燕红等[22]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在距今13000 万年的始孔子鸟化石的羽毛印痕中发现了β角蛋白,并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相关成果,由此证明某些蛋白质成分可以存在上亿年之久。
邢立达等报道的包裹于琥珀中的鸟类翅膀与恐龙尾巴,其保存状态自然是大多数开放体系中的化石所无法比拟的。虽然从其中提取DNA 的可能性为零,但是检测出蛋白质成分则完全有可能。恐龙尾巴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黎刚利用同步辐射X 光荧光成像方法及吸收谱分析,检测到了高水平的二价铁元素,在生物体中二价铁通常来自于还原环境下的血红蛋白和铁蛋白,琥珀中保存的高水平二价铁说明这段尾巴被非常迅速地包裹于无氧环境下,加之动物尾巴和翅膀末端生长的肌肉组织和脂肪组织通常非常少,因肌肉和脂肪分解产生的破坏性物质就比较少,由此可以推断,这条恐龙尾巴和那个保存状况相似的鸟类翅膀很有可能残存了多种蛋白质成分。
每一种蛋白质只能反映很少一部分遗传信息,因此我们不可能依据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来复活整条恐龙,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侏罗纪公园。但是就科学兴趣而言,我们毕竟又向前迈了一步。近二十年来,我国学者主导的关于恐龙和鸟类系统关系的研究,已经揭示鸟类实际上就是从恐龙的一个支系中演化出来的,鸟类的基因组中必定还有大量的源于恐龙祖先的基因。通过分析恐龙的形态以及该种形态在鸟类中相应部分的基因背景,生物学家是有可能通过改变鸟类的基因来“创造”具有恐龙特征的鸟类的,这便是美国学者Horner 数年前宣扬的培育“恐龙鸡”的基本思想。2015年,美国的Bhullar 等在《演化》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通过影响鸡喙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可以产生类似于恐龙嘴巴的宽阔的鸡喙和上颚。这项研究实例说明,培育具有某些恐龙特征的“恐龙鸡”并不是科幻小说。
我们不可能克隆一个侏罗纪公园,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有可能创造一个现代的“恐龙鸟”乐园,甚至是一个“恐龙鸟”餐厅。如果邢立达等同意,可以把那块含有恐龙尾巴的琥珀溶解,然后用蛋白组学的方法分析出其残存蛋白的氨基酸序列,根据氨基酸序列反推其基因,再利用现代成熟的基因工程方法,就可以生产出表达了恐龙角蛋白和胶原蛋白等蛋白质的鸡爪子或鸭脖子。而至于这种鸡爪子和鸭脖子的味道吗,当然红烧的还会是红烧,麻辣的依然是麻辣。
| [1] | Xing L, McKellar R C, Xu X, et al. A Feathered Dinosaur Tail with Primitive Plumage Trapped in Mid-Cretaceous Amber[J]. Current Biology, 2016, 26(24): 3352-3360. |
| [2] | Xing L, McKellar R C, Wang M, et al. Mum⁃ mified precocial bird wings in mid- Creta⁃ ceous Burmese amber[J]. Nature Communi⁃ cations, 2016, 7: doi: 10.1038/ncom⁃ ms12089. |
| [3] | Schmidt A R, Jancke S, Lindquist E E, et al. Arthropods in amber from the Triassic Period[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37): 14796-14801. |
| [4] | Poinar Jr G O, Cannatella D C. An Upper Eocene frog from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aribbean biogeography[J]. Science, 1987, 237: 1215-1217. |
| [5] | Sherratt E, del Rosario Casta?eda M, Garwood R J, et al. Amber fossils demonstrate deep-time stability of Caribbean lizard communitie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32): 9961-9966. |
| [6] | Daza J D, Stanley E L, Wagner P, et al. Mid- Cretaceous amber fossils illuminate the past diversity of tropical lizards[J]. Sci⁃ ence Advances, 2016, 2(3): e1501080. |
| [7] | MacPhee R D E, Grimaldi D A. Mammal bones in Dominican amber[J]. Nature, 1996, 380(6574): 489. |
| [8] | Ostrom J H. Archaeopteryx and the origin of birds[J].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976, 8(2): 91-182. |
| [9] | McKellar R C, Chatterton B D E, Wolfe A P, et al. A diverse assemblage of Late Cretaceous dinosaur and bird feathers from Canadian amber[J]. Science, 2011, 333(6049): 1619-1622. |
| [10] | Prum R O.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ary origin of feather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 1999, 285(4): 291-306. |
| [11] | Navalón G, Marugán-Lobón J, Chiappe L M, et al. Soft-tissue and dermal arrangement in the wing of an Early Cretaceous bird: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avian flight[J].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 14864. |
| [12] | Borkent A, Grimaldi D A. The earliest fossil mosquito (Diptera: Culicidae), in mid- Cretaceous Burmese amber[J]. Annal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4, 97(5): 882-888. |
| [13] | Higuchi R, Bowman B, Freiberger M, et al. DNA sequences from the quagga, an ex⁃ tinct member of the horse family[J]. Na⁃ ture, 1984, 312: 282-284. |
| [14] | P??bo S. Ancient DNA: extraction, characterization, molecular cloning, and enzymatic amplific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9, 86(6): 1939- 1943. |
| [15] | Golenberg E M, Giannasi D E, Clegg M T, et al. Chloroplast DNA sequence from a Miocene Magnolia species[J]. Nature, 1990, 344(6267): 656. |
| [16] | DeSalle R, Gatesy J, Wheeler W, et al. DNA sequences from a fossil termite in Oligo- Miocene amber and their phylogenetic implications[J]. Science, 1992, 257 (5078): 1933. |
| [17] | Cano R J, Poinar H N, Pieniazek N J, et al.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 of DNA from a 120-135-million-year-old weevil [J]. Nature, 1993, 363(6429): 536. |
| [18] | Woodward S R, Weyand N J, Bunnell M. DNA sequence from Cretaceous period bone fragments[J]. Science, 1994, 266 (5188): 1229. |
| [19] | Gutiérrez G, Marin A. The most ancient DNA recovered from an amber-preserved specimen may not be as ancient as it seems[J].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998, 15(7): 926-929. |
| [20] | Allentoft M E, Collins M, Harker D, et al. The half-life of DNA in bone: measuring decay kinetics in 158 dated fossils[J]. Pro⁃ 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2: rspb20121745. |
| [21] | Welker F, Collins M J, Thomas J A, et al. Ancient proteins resolve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Darwin/'s South American ungulates[J]. Nature, 2015, 522(7554): 81-84. |
| [22] | Pan Y, Zheng W, Moyer A E, et al. Molecular evidence of keratin and melanosomes in feathers of the Early Cretaceous bird Eoconfuciusorni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49): E7900- E7907. |